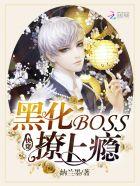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让朕吃口软饭吧今夜无风剧透 > 第35章(第1页)
第35章(第1页)
六公主叶灵落水后,高烧昏迷了三日,醒来后也一直做恶梦,太医说是惊惧导致,皇后就这么一个女儿,心疼的一整个寿宴眼睛都是红的,也没有精力去追究其他,一散宴就往自己宫里走。
叶灵恐水惊悸的症状越加严重,时常梦见自己溺水,梦里有水鬼,皇后惊疑不定,铤而走险找了李尚书,弄了几个和尚进宫念经驱邪,老和尚不管用,她又想找道士,凤仪宫中的动静实在太大。
皇帝愠怒不已,以前朝宗教祸国之事驳斥,太后从中周旋,念皇后一片慈母心肠,最后只不痛不痒的罚了七日禁足,将那些和尚道士关进了地牢,只是朝中对宗教打压甚重,听闻连普陀寺的香火都快要断了。
太后寿宴过后一连半月,皇帝不是在乾元宫歇了,就是宿在洛华宫,皇后犯戒在前,太后心中不喜也不好说些什么,宫妃们也不敢置喙。
只是祸国妖妃重新盛宠的谣言到底甚嚣尘上。
国子监照常上课,谢玉舒大抵病的很重,一整个月的课程都由赵允升代上,皇后之事出后,皇子公主们也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当出头鸟触眉头,国子监难得凑齐了学生,连清晨的朗读都整齐了不少。
谢玉舒病好了之后,也没来国子监,而是被陛下派去随大皇子修复文书。
上完文课之后,叶煊还要去隔壁演武场上武课,教武课的是禁军都统,叶煊刚来,又表现出什么都不会体力还很弱的样子,于是——别人骑马射箭,他在扎马步;别人分组对练,他顶着水碗踩梅花桩;别人与禁卫军蹴鞠比赛,他学着基本功还得当便宜裁判。
外功的基础功太累人了,叶煊纵使有内功傍身,也依旧觉得浑身酸痛,每天回到文渊殿只想倒头就睡,澡都是泰安拿树杈子当武器逼着他去洗的。
这样一来,皇帝虽宿在洛华宫,叶煊见他的次数却不多,倒是省的去猜测烦闷。
如此又过一月,京都入秋,叶煊再度见到谢玉舒,是在太医院。
黄莽无事可做,来演武场抢了卫都统的职务,非要来教导他们,还是自缚双手的一对一车轮对练,美其名曰增加实战经验。
卫都统每天都在水深火热中,也是想要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只是自己不敢,如今有个大老粗送上门来,自然乐意之至,退到一边说是当裁判,实则是看热闹。
宫里的皇子皇女都细皮嫩肉没吃过苦头,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合起来都不一定能打赢黄莽一只手,除了出其不意的三公主外,其他人等均负伤惨败,还受到了黄莽无情的嘲笑。
叶煊没有动用内力,单靠这近来学习的外功与黄莽周旋,在要受伤的关键时刻退出战场认输,因此只有手肘有些擦伤,不似四皇子、五皇子那般狼狈,甚至还获得了在场第二的高分。
黄莽叉着自己的粗腰,笑声如震雷,将御马监的黄维仁都惊了出来看热闹。
就听他道,“你们这一群加起来还没有俺军营里六七岁的小娃儿经造!太弱了!”
五皇子不服气,瞪着这五大三粗的汉子,“黄将军辱煞我也,六七岁的奶娃娃怕是连剑都拿不稳!”
“对啊,他不拿剑,他拿匕首。”黄莽不知道想起了谁,满脸的络腮胡遮挡了脸上的笑,眼睛却高兴的眯成了缝,大声道,“他四岁习武,六岁内功小成,若不是俺们将军不让他去战场,他如今怕也是个满身功勋的少年将军了!”
五皇子冷哼,并不信他,四皇子也认为他是在吹牛,激他道,“黄将军口说无凭。”
“无凭就无凭吧。”黄莽摸了摸自己的大胡渣,不再说这个话题。
黄维仁靠着树,不知道什么时候捧了把瓜子,嗑着看戏,脸上是明晃晃的幸灾乐祸,完全不在意面前这一群是什么尊贵的皇子。
卫都统没那么大的胆子,赶紧解散了课,让各自的太监宫女扶他们去看太医。
叶煊身上的伤也就意思意思,完全是再不上药就快消失了的状态。
但他也不欲做那个特殊的人,免得遭人记恨,慢慢悠悠的跟着最后一个进的太医院。
一进去就见偏院小道有三人相携出来,一人身穿浅白衣衫,看着就是富贵的世家公子,身上配饰不知凡几;中间那人一身皇子朝服,胸前绣着紫貂,已至弱冠;那两人正说这话,多半是中间的人在说,边上的人在听。
最后慢一步跟着的人拿着把折扇遮着脸,眼眸眯起,眼神发散,明显没有在听。
叶煊分别认出三人,微微一怔。
姜鹤不耐听大皇子和谢玉舒口中的那些朝事,深觉得无聊,又不好表现出来,只得拿扇子遮了遮自己的哈欠,视线随意一扫,就看到一个熟人。
他眼中露出真实的笑意,合扇在掌心一敲,就迎了上去,“七殿下!”
交谈的两人话头齐齐顿住,也看到了站在那边的叶煊。
叶煊一一见礼,“大皇兄,姜翰林,谢先生。”
姜鹤高高兴兴的拉着叶煊说话,大皇子叶灼神色淡然点头。
唯有谢玉舒满脸讪讪,颇有一种做了坏事逃跑,却终究被逮到的尴尬。
他几次张嘴又闭上,最后心如死灰的开口:
“小臣……见过……七皇子。”
面如冠玉的少年一开口,吐出一口公鸭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