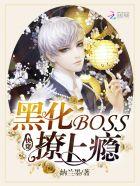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新不了情吉他谱c调简单版 > 第17页(第1页)
第17页(第1页)
她身旁的女生看样子没大我几岁,头发染成彩虹色,穿着件黑体恤和大短裤。她长得很漂亮,漂亮的很有攻击性。如果说何南是小家碧玉型,那她就是御姐型。结果开口却是搞笑女。“馁吼哇,我嘿鹅贼。”我愣了下,何南跟何北抱着肚子笑个不行。“你好我是苏浔,你是广东人?”“表姐你别逗苏浔啦。”“开个玩笑,我是海城人。”女生道,“你好,我叫何执。为何的何,执着的执。”我突然感觉自己很幸运,如此社恐的我头一次面对着这样一大群陌生人没有怯场,我和他们明明刚刚认识,却能在酒桌上谈天说地,像是好久不见的老友。跟何执聊天后我才知道她是一个自由摄影师,偶尔给人拍拍婚纱照,偶尔去照相馆帮朋友拍几张证件照修修图,大部分时间在旅途中,拍拍自己喜欢的东西,拿回去做成艺术展览。“曾母暗沙五彩斑斓的珊瑚礁,新疆光怪陆离的戈壁和大漠孤烟,茶卡盐湖碧波无垠,它们都被我定格在相机里了。”我能看见,何执在谈到她的摄影经历时眼里的兴奋,她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这次来漠河,高低出几张神图,做成微电影眼红死工作室那帮小孩。”她眉飞色舞地说着。我只觉着她很可爱,又可爱又古灵精怪,活脱一个鬼马少女。我就着她的工作和她聊了许多,又给她看我手机里拍过的照片。“这个挺好。”我给她来回翻着。“诶呦呦这张不错,小浔你挺有摄影天赋的啊。”我在一旁不好意思,“其实我挺喜欢拍照的。尤其是风景照。”她在一旁认真看着,时不时和我讨论照片里的人,建筑,街道。“咱俩挺像的。我看这么久,没看见你一张自拍照,我也很少自拍。”我点点头,我确实不喜欢自拍。我跟何执正说着,旁边的何南拍了拍我俩。“你俩研究什么的鬼鬼祟祟的。”“我跟苏浔探讨人生大事呢别来沾边。”“你还探讨上人生大事了,你一天神出鬼没的除了照相还有什么大事啊你。”何南对她姐这形容给我逗乐了,我想起高三的时候我同桌经常说我神出鬼没。自习课上,我经常去找老师答疑,座位上半天看不见人影。饭桌上大家再次举杯,说说笑笑。有时候我觉得,我的人生应该也是这么过的,我需要自由,无边无际的自由。在不同的地方记录下当地的风景,和一群热情真诚的人日饮夜饮,不醉不归。曾经的我也这样想过,除了自在和自由,没有什么需要我驻足停留。可后来我和曾洺在一起,他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爱。那是在我心里唯一可以和远方的田野相提并论的东西。我爱自由,成了,我,爱,自由。出事派出所的工作繁杂但并不枯燥,我们几个人分工明确,这里的每个人看起来嘻嘻哈哈的,但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尤其是何北,他每周工作之外都会进行一次走访,走访内容是百姓生活幸福指数。他说,在派出所实习这一年,他越发认为检验工作完成结果的标准不是上级领导的表扬和年终的荣誉证书,“是百姓对待咱们派出所的认可度高不高,换句话说,大伙到底信不信任咱们,遇到难事能不能第一时间想到咱。”我觉得,何北他们这一年做的努力是有效果的,我刚到漠河打车,那司机一听我要去派出所,就跟我打开话匣子说了起来。他说现在派出所上班的人不多,但那几个小年轻啊,都是各顶各的棒!什么老李家的鸡和鸭丢了,什么邻里之间纠纷,什么谁家往谁家门口扫雪了,派出所的年轻人都去帮着劝和,帮老百姓解决困难,解决他们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而不是纸上谈兵,空谈一气。司机说,自从前年派出所新招了一批小年轻,那条街附近小偷少了,抢劫的也少了。这天,何北带着我还有其他办公室两个人一起出访。“我们要去的那家,家庭矛盾有点严重,事有点不好办。”走在前面的何北和我说,“我跟小夏他们半年前处理过他家的事情,很麻烦,你在一旁做笔录录像就好。”派出所附近都是回迁楼和棚户区,老旧的单元楼上写了大大的“拆”字,我们走到楼下时,听见楼道里传来一句接着一句咒骂声混杂着女人的哭声和摔东西的声音。我以为自己要亲临家暴现场了,结果身旁的夏彤跟我说,一准是这家的败家弟弟回来要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