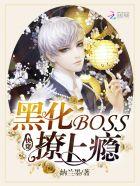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晨曦之雾实体书番外 > 第75页(第1页)
第75页(第1页)
但是林医生为她谋了一个他的助手的职位,每天要做的工作很少,但是行动却比义工自由得多。她并不敢总出现在外公的面前,但她永远停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早晨看着他佝偻着腰散步,打太极拳,中午看着他与病友下棋,傍晚他与她相距几百米远,观赏同样的夕阳落山的美景。陈子柚在工作中认识了不少病人,有一些将她当作好朋友,会向她倾吐很多心事。她并不是个善于交际的人,少女时代便不是,成年后这种机会更是被扼制了。在她的生活中,几乎只有自己与影子相伴,即使身处纷纷扰扰热闹非凡的环境中,也始终像一滴误落水中的油,总是格格不入。可是在这种非正常的环境里,她却有了真正融入其中的感觉。那些看似或疯疯癫癫,或痴痴傻傻,或神神叨叨的男男女女,内心深入各有自己的一个小世界,而她居然能够体会。陈子柚陪伴的病人里有一位年轻时作过舞蹈演员的老人,每天都要教她几个舞蹈动作,她到目前为止已经掌握了新疆舞、蒙古舞、印度舞还有糙裙舞的要领。其实求学年代她只学过芭蕾与国标舞。另有一位男病人,每天要求她用英文与他交谈十分钟,内容无所谓。还有一位只有七岁的可爱的小男孩,因为目击父母的车祸受到惊吓。陈子柚每天去看他,不言不语,没有表情,但是当她离开时,他会哭闹不休,后来她改到晚上去看他,陪他不言不语半小时,等到他犯困了便哼着歌哄他入睡。还有四五位老人,每天聚在一起唱陈年的老歌,用手风琴伴奏。某日手风琴手生病了,剩下的人坐立不安,心情烦躁,看着那闲置的手风琴,每个人都仿佛要发病的山雨欲来状,这种乐器陈子柚是学过的,虽然不太熟练,于是她替他们伴奏了半个下午,此后他们常常邀她作听众与评委。她越来越适应这里的生活了,如鱼得水。也许,她自己本身也是这个族群中的一员。她不免这样想。融入这个族群的好处是,在她还小心翼翼地与外公保持着最安全的距离时,孙天德老人竟主动地与她接近了。第一次他说:&ldo;你调到这里工作了吗?这护士制服很适合你啊。&rdo;第二次他说:&ldo;你的眼睛肿了,是不是昨天晚上睡觉前喝水了?&rdo;第三次他说:&ldo;姑娘,你最近又瘦了。&rdo;再后来,他在夕阳落山后的幽暗天幕下发现了她,便邀请她第二日一起看日出。她打了申请报告,每日天不亮便在医警陪伴下,陪着老人一起等待日出。但那几日清晨总是大雾弥漫,他们等了整整七天,才终于看到一次真正的日出。当那个犹如腌蛋黄一般娇嫩的小小的太阳轻轻跳出黑色云层,也映红了老人的侧脸时,陈子柚的嘴里泛出咸咸涩涩的味道,原来她的泪水不知何时滑入了唇角。此时的一切都如同极地的冬天里沉寂于黑暗中的黎明时分,四周乌压压的一片,偏偏如此的静谧,如此的详和,明知前方没有未来,明知即使天亮了也仍是漆黑的一片,却还是忍不住期待一点点的光明。其实,按医生的说法,她的外公的情况越好转,便证明那颗肿瘤的破坏作用越在回光返照式地发挥着邪恶的作用。老人现在这种样子,不只发病时狂暴的气息无影无踪,甚至在他的健康状态时,也不曾这么安详而从容。陈子柚几乎怀念起过去外公发病时几度要致她于死地的情形。那时她只是伤心,但不曾绝望。那日傍晚她在医院里看见了江流,一闪而过然后消失不见,似在躲她一般,让她几乎疑心自己看错。她盯着江流消失的方向很久,与她一起看夕阳的外公突然凑过来说:&ldo;你认识那小伙子啊?&rdo;&ldo;呃?&rdo;&ldo;他以前也来过一两次。刚才你没发现他时,他看你很久了。&rdo;&ldo;哦。&rdo;&ldo;他是不是喜欢你?&rdo;&ldo;不知道……不会吧?&rdo;&ldo;你这样的姑娘,如果我是小伙子,我也打算追求你。&rdo;&ldo;咳咳。&rdo;陈子柚被呛到。&ldo;你有男朋友吗?&rdo;&ldo;……算是有吧。&rdo;她突然被吓到,于是言不由衷地说了这么一句谎话。晚上她拨电话给江流。这个号码她一直能背下来,但从来没有存入手机,也从未主动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