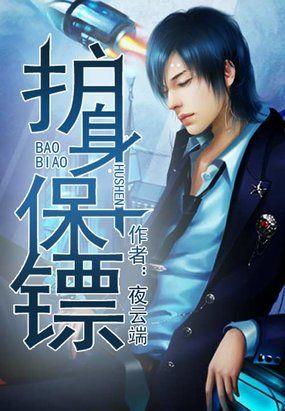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进击的巨人利艾车图 > 第29页(第1页)
第29页(第1页)
你认为这就是结局了吗?
伦敦的天是苍白色的,刚下过一场雨但是没有转晴,依旧摆脱不了一层雾的印象。利威尔穿着一身便装走在路边,十字路口的某个年轻车夫脱帽向他行礼,为的大概是某次临时出行时他随手给予的几便士恩惠。
被人记住并且在再见时认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男人微微点头便从他身边走过。他们总是伪装得跟人类一样,衣食住行,却不会生老病死。他们在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然后在跟周围所有人事变得熟路之前再悄悄离开,让人们在依旧推进的时间里渐渐淡忘他们不老的容颜。
也许很多年以后,已经长大的小姑娘偶尔会想起有一个金发的漂亮姐姐曾在这个街角将几颗水果糖放在她手心,一个走起路来很刻意模仿主人的执事先生会撑着一把黑色的伞,站在路灯下面抖着报纸。还有两位笑起来很亲和的先生会在周六的傍晚陪广场上的男孩儿们玩弹珠,然后去一家不知名的静吧喝上两杯。他们的姓名隐藏在不动声色的岁月背后,等有人发现他们已经远去的时候,大概会猜测,噢,又是一场不知目的地的旅行。
他们又决定要离开了。
利威尔比约好的时间还早到一些,他点了一支烟。这幢已经搬空的房子和地下锁上的花园好像都变得与他无关,他站在路灯下面等待着这场计划好的告别。他听见马车在不远处停下,有人小跑着靠近。血族高于常人的听觉放大了对方随着脚步的喘息,那感觉就像他的呼吸在耳边。
他看见了他,年轻的耶格尔。仿佛已经完全翻过了前些日的阴霾,对他来说没有长久的苦愁表情会挂在脸上。他,举止端正,眼神明亮,他是一种利威尔无法企及的可能性。
就像光,未知,和希望。
“利威尔先生……等很久了吗?”
“并没有。”
有这样的告别本身就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了,这在过去的世纪中是不存在的形式。说走就走的人有了牵挂的东西,于是他就丢失了绝决。利威尔看着夜空中月亮的样子,想起了它在泰晤士河中的倒影。月光晃晃,水波一层一层推向黑色的河面看不见的尽头。有人说他感谢重生,他说他从不恐惧未知,他口中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曾是单调的黑白色。
“那,到底是什么事情这么急呢?”
“艾伦。”
哪怕再多否定,再多错过,再多遗憾。有诅咒的地方必然有祈愿。大概就是这样吧,他的真挚,他的坦诚,他的人性中的善和美打动了你包裹内心的坚韧墙壁。你知道这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唯一,但是偏偏是他,偏偏是他,他对你来说变成了唯一。从他主动献血之前警钟就已经敲响,他唤醒了你刻在灵魂里的饥饿感,你明明是渎神者,却不想他成为守灵人。早该害怕了吧,一双绿眼睛看穿了你要隐藏的所有岁月年轮,斑驳的,卑微的,孤单的。所以现在你要将他放回留白的位置,这真是一个自私又伟大的决定。
“你想过去远方旅行吗?”
“哎?”
你一定想过独占他的人生,将他变得和你一样,这也许是有人愿意看到的结局,但这总是不对的。你知道放他离开会比留他在身边的意义多得多,你也知道他已经带给你足够——在你时间停止的身体里开出扎满倒刺且蔓生皱纹的爱、悔恨,以及,血肉模糊的救赎。
“我们要走了。”
“……我们?”
“看着我,艾伦。”
他小心翼翼地回问,眼中闪过不安,你并没有犹豫,哪怕你发过毒誓,不再对他使用这招。可是现在,你强迫他看着你的眼睛,然后他便再无法逃脱,如被下了束心蛊咒,只能任你摆布。这个过程是及其艰难的,对于内心。特别如果,再加上一句他以颤抖嗓音说出的——
“满意了吗?!”
“我必须走了。”
“但您没有必要这么做!”
你突然想起了初次见面的那天晚上,也是这样昏暗的街道,灯光也是这样正好的角度,把你留在黑暗中,光却落满了他面容。你能看清他瞳孔里的纹路,他还一直试图分辨你的表情。但是现在,他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此时此刻那双漂亮眼睛中只剩下模模糊糊的轮廓。
“我会恨你的,利威尔……你不能这样做!”
他急切得连尊称都忘记了,1882年7月2日零点,男人掐灭了最后一支烟。轻轻拥抱了一下面前的年轻人,他微微仰头,在他唇角留下一吻。青年的表情很丰盛,不同于任何一个他过去见过的面临死亡的人,却要更加挣扎和绝望。可是总有人坚信忘却比牵挂好过,记忆只需要一个人留守就还是存在的,希望总该彻头彻尾干干净净被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