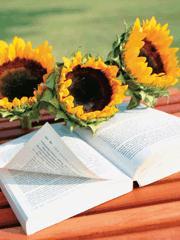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闲唐 txt > 第45页(第1页)
第45页(第1页)
李德謇见李元婴这般模样,也不催促,由着他走走停停,慢腾腾地行到村头。
还未走近,李元婴便看到村头有株几人合抱才抱得过来的老树。此时那株婆娑的老树下有朗朗诵读声传来,细听隐约能听到“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之类的,竟是前朝逐渐流传开的《千字文》。
李元婴初启蒙时学的也是这个,全文由近千个不相同的常用字组成,既能帮初学者认字,又把许多道理与典故编了进去。
李元婴好奇地走过去一看,发现树下立着个和李治差不大的少年,约莫十一二岁,手里拿着卷书在教导几个齐齐整整坐在树下的小孩。
他们有的带了个蒲垫,有的直接席地而坐,年纪约莫是十岁左右,全都认认真真地挺直腰听那少年口齿清晰地带他们念千字文。
李元婴觉得真稀奇,这么个十来岁的少年人怎么成了夫子?
那少年并未注意到李元婴等人由远而近,他拿着块黑漆漆的木炭把字写在树身上给同伴们看着学。旁边有条小溪,每教完一个字,那少年便用水把字洗掉,再写别的字。
李元婴驻足看了一会,那少年才注意到他们一行人的到来,停下讲解上前拱手问:“几位客人来我们唐家村可是有事?”
树下坐着的村童们都好奇地看向李元婴几人,觉得李元婴的衣着华贵得很,身边跟着的几个禁卫也特别气派。
李元婴像模像样地拱手朝为首的少年还了一礼,也不隐瞒,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来寻孙老神医的,家中长辈有疾,想请孙老神医替他瞧瞧。”
少年道:“那来得倒巧了,要是再过几日,孙老神医就不在我们这儿了。”说罢他让其他人先背一背刚才教的那几句,亲自引李元婴一行人入村。
李元婴对这少年很有好感,直接自报家门:“我姓李,名元婴,你叫我名字便好,你叫什么?”
李是陇右大姓,遍地都是李家人,少年不曾多想,只觉李元婴兴许是哪个权贵人家之子。
少年不卑不亢地答道:“我姓唐,单名一字璿,还未取字,你也叫我‘阿璿’便好。”
李元婴点头,顺势问起唐璿刚才在做什么。
唐璿告诉李元婴,他家中比村里其他人宽裕一些,家里人舍得送他去读书。他认为村中的伙伴们虽都家贫读不起书,能认几个字也是好的,即使能去考科举的人寥寥无几,出去受雇佣时也算有个一技之长,指不定能多拿几个工钱。
于是唐璿总趁着休沐时给同村伙伴们教几个字。
一篇《千字文》,他已经教了大半了,自己也把千字文记得更牢了,算是利人也利己!
李元婴道:“你真了不起。”
唐璿摇头道:“只是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而已。”
李元婴由衷夸道:“便是力所能及之事,也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你太棒啦。”
这样直白的夸奖让唐璿有些脸红,他腼腆地笑了笑,指着前头一处简陋的农宅说:“孙老神医就住在这儿,最近他在教村里人采药。”
周围山多林多,药材也长得好,学会采药对村里的人来说是个很不错的新进项,所以村里人每天都聚在那处农宅中学习如何辨认药材、如何在采集和晾晒药材过程中不损伤药性,也就这两天孙思邈说要进山采药才冷清些。
唐璿和李元婴说了这些事,补充道:“昨天孙老也进山了,不知有没有回来,若是没回来的话你怕是要等一等。”
李元婴爽快地道:“我等得的。”
唐璿点头,上前帮李元婴叩门。
连敲几声,里头都没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