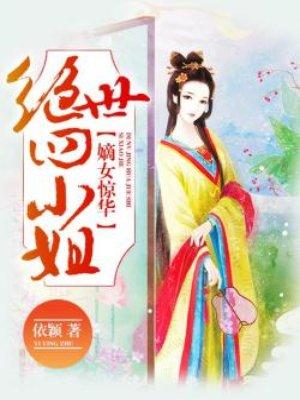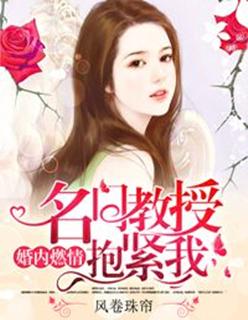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德国和奥地利统一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工会施加主要影响的领域是参与联合决定或共同决定。这同德国在1919年到1933年就已盛行而在投降后又开始在各地自发出现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密切相连。工厂委员会由一个工厂里全体人员(雇主除外)选出,所以通常包括不止一个工会的成员。这样,按照传统和章程,工厂委员会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工会的竞争对手,也必然成为以一个工业为基础组成的工会的竞争对手。英国人和美国人担心工广委员会可能落入左翼分子的手中,而且可能建成一种与效忠的工会相竞争的组织;俄国人则把工厂委员会视为增进工人阶级团结的一种手段。如何对待工厂委员会的向题被迫提出来了,因为有些委员会的成员,按特有的德国方式迫切要求象魏鸩共和国时湖那样确定该组织的法律地位,于是盥自管制委员会柱1946年1月10日的第二十二号法令中对此作了规定;工广委员会的组成不是强制性的,按照法令要求,其明确的权利与职能只限于在工厂一级主持劳资双方谈判。但为了防止两种形式的组织发生冲突,法令坚持要工厂委员会与工会密切合作;西部的工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企图通过公布一项与个别雇主签订的&ldo;模范协议&rdo;来确定工厂委员会的地位,并且开展活动来保证工会会员在工厂委员会内取得席位。这样就使共产党人的希望落了空,他们原来想利用工厂委员会去重新取得因受工会运动发展的影响而被剥夺了的对工人的控制。然而英方的人力管理处担心,在德国组织起来的劳工事业可能因工厂委员会的发展而遭到削弱,并非获得加强,事实证明这种忧虑是有些道理的。&ldo;你们的工厂委员会不是从工会运动中产生的,……〔它们〕是依靠本身的权利,根据一项法令并在该项法令的……培植下建立起来的,因而在你们面前提出了一个问题,要在你们的组织上进行移花接木。&rdo;德国工会联合会成功地把工厂委员会置于恰如其分的严密控制之下,但工厂委员会仍然是在单个工厂内照管工人利益的组织,而工会在一般工人看来则是在高一级起作用的外部组织,使人感觉到它主要是收集捐款的。同时,工会的利害关系所在及其对雇主的不信任导致它要求获得的管理权力,远远超过英国工会参与共同协商的权力范围。在英国当局看来,这又是危险的,而且野心太大了。德国人却回答说:情况有所不同,英国制度的用意是信赖雇主们的诚意,而这种情赖在德国是不存在的。这种心情在汉斯&iddot;伯克勒于上面提到的会议上回答卢斯先生的话里作了很好的说明:我们谈到工人在作出决定时应享受平等待遇,并非是空喊口号。我们想争取这种平等是有其最紧迫和最现实的理由的。我们毕竟生活在二十世纪这个充满前所未有的事件的时代里。工人再也不愿容忍任人摆布的境遇了。必须记住,两次大战及其产生的后果把我们德国经济的缺陷完全暴露了出来。把我国人民和全世界引入两次大战并造成如此可怕后果的,并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不管是政治领导还是经济领导。既然我们总是被迫承认德国的雇主阶级目光短浅、顽固不化,既然我们下定决心不再被引进我刚才说到的那种可怕的情景中去,田此我们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我们的权利。正因为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决不会象我们雇主那样心胸狭窄、顽固不化、目光短浅。
根据&ldo;模范协定&rdo;,要同工厂委员会协商的不仅是有关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等问题,而且包括人员配备和晋级提升等一切问题,协定还要求雇主向工厂委员会就生产程序和生产计划提供定期报告,并让工厂委员会查看公司的帐目。这些权利后来进一步得到扩大,在非卡特尔化的工业中更是如此;&ldo;联合决定&rdo;在战后己取代了工业的社会化。成为西德有组织的劳工所主要关心的事了。
它虽然不完全受到雇主的欢迎,但在德国经济恢复时期确实有助于避免劳工的骚动。要不是这样,可能容易出现持续坚持提高工资的要求。
1946‐1947年冬,由于工会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反抗只对共产党人有利,所以它们对工人们施加了一种可贵的起抑制作用的影响。但是,为了保持对会员的影响,它们不能落得个唯命是从地与盟国消极合作的名声。的确,从很早的时候起,工会就坚持不懈地要求改变盟国的政策。工会发出了下列呼吁:停止拆毁可以用于和平目的的工厂,彻底整顿粮食分配机构,迅速追返战俘,把行政职权交还德国当局。如果认为因为这些工人是反纳粹的,是反共的,他们甚至在有关工业组织问题上也和英美人意见一致,这将是一个错误。恰恰相反,他们同别人一样热衷于使自己的国家从盟国的控制下解放出来,而对于上述那些问题,他们首先是站在德国人的立场上去考虑,然后才站在工人的立场上去考虑。
第二节教会
因参与1944年7月20日事件而被处死的忏悔教会领袖迪特利希&iddot;邦赫费尔在1941年向一个朋友承认,他正在为他的国家的失败而祈祷,因为他认为这是德国用以抵偿它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唯一方法。决不是所有的德国教职人员的态度都和他相同:有一批人一度则被纳粹钓饵的票面价值引上了钩,真以为国社党会帮助教会达到它的目标;有些时候,这种幻想历久不灭。许多教职人员坚持教会应超然于政治之外的传统观念,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准备按这个极权主义国家的要求而对之绝对效忠;当然,许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抵抗。因此,他们对盟国的胜利,普遍报之以拯民于水火的颂歌。盟国的胜利也因那些曾在新教教会掌过权的德国基督教徒迅速销声匿迹而被欢呼;他们的领袖米勒主教自杀了,余下伪人以罕有的谨慎退居幕后。象工会一样,教会也很明白,它们内部的勾心斗角妨碍了它们对国家社会主义所进行的抵抗。第三帝国的经历使它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且普遍地渴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不让这种团结烟消云散。甚至在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也有了友谊和合作,虽然因为不可能存在具有那种水平的思想统一,在新教教徒内部发生了一种最为重要的变化。1945年8月底,符腾堡的主教武尔姆召集了所有可以邀请到的教会领袖在特赖萨开会,决定把新教教会生活中三个最重大的运动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团体‐‐德国福音派教会。这三大运动就是武尔姆本人于1941年创建的&ldo;教会阵线&rdo;、&ldo;忏悔教会&rdo;以及巴代利亚、符腾堡和汉诺威的所谓&ldo;完整的&rdo;教会。后者曾经避免在1933‐1934年间被迫把国家社会主义的支持者塞入他们的宗教会议。选出一个十二人的理事会作为临时的&ldo;教会政府&rdo;,而永久性的教会制度则被推迟到时局较为稳定的时候再行制定。德国所有主要的路德派、改革派和联合派教会都接受这一决定。实际上,忏悔教会希望立即实行彻底的改组,而保守的路德派则厌恶任何革命性的背离旧宗教的改革信条,上述决定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妥协。作为组织成员的教会都保留其自主权,然而单一的组织机构是为代表大家去行动而建立的,其结果是稍胜于一个联合会而略逊248于一个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