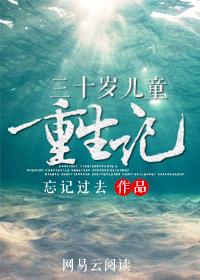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重生明朝朱由检的(我爱肥猪猪) > 第70章 祖大寿调任大同(第1页)
第70章 祖大寿调任大同(第1页)
几天后,兵部升孙繁祉为蓟州游击的公文送到了三屯营,而孙祖寿派往大宁,也就是现在的可岢河套的信使也得以重新出发。
这次去朵颜卫商谈招降的事情,带上了用印后的喀喇沁盟约拓印本。
十多天后,信使重新返回三屯营,带来了与朵颜卫的新盟约。
新盟约没有谈下大宁的哨点,但谈下了其它哨点,并允许明军夜不收前往大宁附近哨探。
至于大明这边付出的代价,除了允许他们来遵化马市交易物资外,还每年给予两万两银子、十万石粮食的岁赐。
仅次于大明最关心哨点之事外的战马,双方也约定了每年不低于两千匹马的数量,价格跟喀喇沁商谈后的一样,战马二十两银子,驮马十两。
至于牛羊等牲畜,也做了相关的价格界定。
这次顺利出使朵颜,意味着大明拉拢喀喇沁蒙古诸部的第一步计划成功实施。
接下来的时间,孙传庭除了继续加强清查整顿蓟州镇的吃空饷、操练与城防外,还有按照皇帝的要求,开始挑选合适的军队去边墙外商议的地点营建哨点。
除了这些固定的哨点,孙传庭自然也不会放过其它可能道路的哨探,他要求每个关隘的守军必须每天派出指定数量的夜不收出边墙,深入北面燕山,进行例行巡查。
当然,孙传庭之所以能够在冀州镇做如此多的动作,除了他的决心与勇气外,还有朝廷能够给冀州镇及时送来充足的钱粮,外加孙祖寿这个曾经就已经在冀州镇做过整顿尝试的总兵全力支持。
。。。。。。
天启八年的春节刚过,身在宁远的祖大寿便接到了兵部的调令,兵部命他二月十五日前必须带着他直属的三千骑兵前往大同镇阳和卫报到。
至于官职,依然还是副总兵,只不过换了个称呼,变成了大同副总兵。
等行人司的官员走后,祖大寿兄弟子侄与妹夫兼大舅子吴襄很快便聚在了祖大寿的两侧。
祖大寿的兄弟祖大弼气呼呼地大骂道:“这袁可立真不是个东西,他在兵部的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急不可耐地要将我们调离辽西了!”
祖大寿的堂弟祖大乐也高声附和道:“没错,朝廷这是想卸磨杀驴,将我们调离辽西后,想卸掉我们手上的军队!”
祖大寿的子侄们也纷纷跟着在后面大声抱怨。
等众人抱怨得差不多后,祖大寿看向吴襄道:“双环,你怎么看?”
被祖大寿点名,所有人的目光立时都转到了吴襄那张帅气的脸上。
今年才三十六的他,正是男性最有魅力的年纪。
虽然他带兵打仗的能力不行,但一大家子的生意与信息来源,可都要靠他。
对于兵部突然来的调令,吴襄心里也是十分的不满与不解。
不满的原因很好理解,那就是他们的根一直在辽东,辽东丢失后,根就转移到了辽西,他们两家都是辽西当地的武将世家大族。
而且,虽然辽西直面建奴的兵锋,但有坚固的城堡在,不善攻城的建奴拿他们根本不会有太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