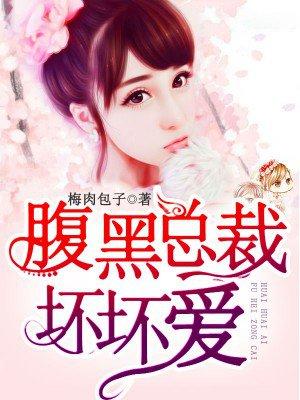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女主一夜死七次剧透 > 第90章 90(第2页)
第90章 90(第2页)
一道刺耳的声音携带嘲讽地响起。
继而是许多人附和的嘲笑声。
柳时镇猛地抬起头。
来人并不是花御礼,而是一群穿着高年段制服的男生。
带头说话的那个人柳时镇并不陌生,因为除了花御礼的缘故,他也在小时候受到了对方好几次欺负。
“车载承。”
柳时镇面无表情的样子像极了花御礼。
他缓缓地开口念出了对方的名字,这个在学校一向以“恶”和“欺凌”出名的高大男生。
车载承低眼看了他一眼,语气蔑视,“你家主人难道没有告诉你什么是尊卑吗——遇到学长不用敬称可不好。还是说,家养狗怎么都听不懂人话?”
柳时镇在瞬间暴起,“想死吗你!”
围绕在车载承身边的人纷纷散成一排,和柳时镇形成了明显的对峙局面。
车载承嘴角一弯,“怎么,你想跟我打架吗?”
柳时镇松开手中紧握着的书包带子,将因愤怒而青筋暴起的左手压在桌面慢慢的站了起来。
明明还只是瘦弱的孩子,却在站起来的时候带来惊心动魄的压迫感。
柳时镇沉着眼眸,冷笑道:“是有如何。”
“被我们打了可别哭鼻子啊小崽子哈哈哈哈!”
…………
被数学老师留了下来商讨了下星期全国竞赛的事情,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上许久的花御礼总算是回到了教室。
然而她一走进教室就发现了柳时镇的不知所踪。
猜测对方可能是去厕所了的花御礼从抽屉里抽出了一本原文小说。
她最近在自修德|语,看的却是波德莱尔的《恶之花》。
一直到把看了好几遍的书又粗略的翻了一遍,花御礼也没等到柳时镇回来。
花御礼眼神一凛,果断地把书拍在了桌上:绝对是出事了。
她迅速地跑出了教室,先到了老师的办公室简练地说明了原委求得了帮助,然后挑出了校园里几个偏僻的地方一一找了过去。
等到花御礼找到柳时镇的时候,他正一个人蜷在体育馆鞍马器材的一边,呲牙咧嘴的嘶着痛。
花御礼静静地站在门口看他。
良久,她才眨了下眼睛对着身旁的数学老师道:“谢谢老师,我们已经找到时镇了,接下去就交给我好了。”
数学老师有些近视,加上事情紧急跑出来的时候也没戴上眼镜,对着缩在阴暗角落的柳时镇身上的伤也看不分明,只问花御礼:“御礼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