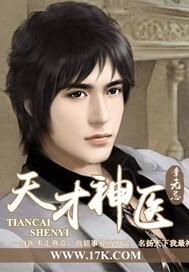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穿成书生郎TXT > 第114章 第114章(第2页)
第114章 第114章(第2页)
得见友人,方俞脸上笑意渐盛,先前也猜测过楚静非的身份,可实在是无从下手,又记得原书里好像没有这个名字,一点都不深刻,他潜意识里觉得可能是个边缘小人物,便当是因缘际会做个结识了,没成想今日竟在此处重逢。
他笑眯眯的看着万年不改冷脸的楚静非,脑子却在飞速旋转,赶紧和京城中的各个官吏匹配。
楚静非未曾自报家门,也不解释自己为何会在这里,却是闲拉了句:“听说你夫郎有孕了。”
方俞下意识就想问,你听谁说的?但这样可能会直接惹恼对方,便道:“承蒙楚兄关切,已三月有余。”
楚静非未有多说什么,忽的转身走了,方俞觉得莫名其妙,正要追上去,耳边便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到这头来赏花了。他当即调转了方向,没在跟上去,待他从小路转回正堂时,外头四处都是交织的男女,寻了一圈也未曾再见到楚静非。
他颇觉怪异,可又不好打听,他觉着时下楚静非这个名字都是假的,但既能进得琼林宴,那高低是官宦人家的子弟,就是不知哪家的。
“方大人,你去哪儿了,我们一番好找,来吃盏酒做首诗吧。”
“素闻方大人文采了得,颇得皇上赏识,今日也好叫大家开开眼去。。。。。。。。。”
方俞突然被一杆子吃了薄酒的贵胄子弟抓了正着,连拉带推的被拖去吃酒作诗。楚静非没寻到,反而落入众矢之的,方俞暗暗骂了楚静非一句,只怕出了风头,一场宴他藏拙扮憨,俨然是一副光会读书写文章的迂腐之态,装足了乡野出身,自偏远之地没有什么见识的土包子。于高处的公主原见着青年才俊拥簇的男子惊鸿一瞥:“皇兄怕是不疼我,分明这榜眼郎形貌最为出彩,竟也未点为探花!”
一旁的嬷嬷缓缓道:“陛下最疼的就是公主了,这琼林宴便是特地为公主所办,就是为了公主能挑选个称心如意的驸马爷。且在看看罢,陛下英明神断,此番自有陛下的思虑。”
果不其然,公主观摩了一阵,见榜眼出尽百宝,地方来的果然没多大见识,摇了摇头。
不枉一番折腾,宴到尾声,方俞眯着醉眼听见有男子呜呼叹息,公主选中了状元郎。
方俞暗自庆幸,今日表演的很成功,不单躲过了公主,也让贵家小姐小哥儿对他全然提不起什么兴致,不过却也算是把“盛名”远播了,一场宴下来,诸人心中对榜眼的总结便是,空有皮囊,绣花枕头,难堪大任,没有见识云云。
虽说各家大人没怎么到场,但很快他的名声也会传到这些大人耳朵里去,方俞心中清楚,应当不会有什么大人同他伸出橄榄枝了。
宴会结束后,方俞回到宅子已然是一身酒气,京城贵少爷们都能喝的很,自诩风流,竟不是盖的。
乔鹤枝在宅子前等到了自家大人的马车,长松了口气,见着车上下来醉醺醺的男人:“怎的醉成这样?快进屋去喝点醒酒汤。”
方俞在乔鹤枝身上蹭了蹭:“我装的。”
乔鹤枝拍了他的胸口一下:“宴上装装也就罢了,怎回家来了还装,当心丢你在外头吹冷风,等酒醒了再进去。”
方俞笑了一声:“可别,我今日逢迎说笑,脸都快僵了。”
乔鹤枝扶着人进府去,伺候方俞一通洗漱,又给人喝了汤水:“今日琼林宴可是贵人云集?夫君这么快就结交到了大人?”
方俞有些不解:“何出此言?”
乔鹤枝取出了个十分精致的乌木盒子,轻轻推到方俞身前:“晚些时辰送到府上来的,京城里没有什么故交,知道咱们住处的人少之又少,且还说是恭贺我有孕之喜。我想着知道如此之多,定然是夫君相谈甚欢的大人。”于高处的公主原见着青年才俊拥簇的男子惊鸿一瞥:“皇兄怕是不疼我,分明这榜眼郎形貌最为出彩,竟也未点为探花!”
一旁的嬷嬷缓缓道:“陛下最疼的就是公主了,这琼林宴便是特地为公主所办,就是为了公主能挑选个称心如意的驸马爷。且在看看罢,陛下英明神断,此番自有陛下的思虑。”
果不其然,公主观摩了一阵,见榜眼出尽百宝,地方来的果然没多大见识,摇了摇头。
不枉一番折腾,宴到尾声,方俞眯着醉眼听见有男子呜呼叹息,公主选中了状元郎。
方俞暗自庆幸,今日表演的很成功,不单躲过了公主,也让贵家小姐小哥儿对他全然提不起什么兴致,不过却也算是把“盛名”远播了,一场宴下来,诸人心中对榜眼的总结便是,空有皮囊,绣花枕头,难堪大任,没有见识云云。
虽说各家大人没怎么到场,但很快他的名声也会传到这些大人耳朵里去,方俞心中清楚,应当不会有什么大人同他伸出橄榄枝了。
宴会结束后,方俞回到宅子已然是一身酒气,京城贵少爷们都能喝的很,自诩风流,竟不是盖的。
乔鹤枝在宅子前等到了自家大人的马车,长松了口气,见着车上下来醉醺醺的男人:“怎的醉成这样?快进屋去喝点醒酒汤。”
方俞在乔鹤枝身上蹭了蹭:“我装的。”
乔鹤枝拍了他的胸口一下:“宴上装装也就罢了,怎回家来了还装,当心丢你在外头吹冷风,等酒醒了再进去。”
方俞笑了一声:“可别,我今日逢迎说笑,脸都快僵了。”
乔鹤枝扶着人进府去,伺候方俞一通洗漱,又给人喝了汤水:“今日琼林宴可是贵人云集?夫君这么快就结交到了大人?”
方俞有些不解:“何出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