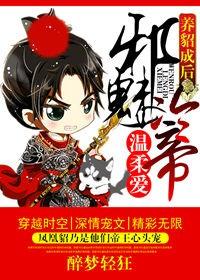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大唐初见有没有第二部 > 第77章 杜荷(第3页)
第77章 杜荷(第3页)
杜构见我不说话怒了,道:“还有九月你就该结业了,就你这样,能过的去?”
我回道:“不是还有九月时间,我自会努力赶上,再说,父亲为何如此看重科考?我不是已经为官了?”‘主事’官职虽小,可我已经很满足了。虽然科举过了对我百利无一害,可我还是有些想不明白,为何杜构一心想着让我做官。
眼见杜构怒地要拍桌,我忙道,“孩儿已不是三岁孩童,分得清好坏轻重,父亲你就不能好好讲道理,别老发火吗?”
杜构听了压了火气,冷笑了声,道:“你若真分得清好坏,会随意派杜安去和孙家合作?是,你是为官了,若那个不入流的职位也算的话。你倒长大了,有自个想法了,那你可解决了那些麻烦事?”
我一惊,他怎么知道我派杜安去为商?还有,他说‘麻烦事’,什么‘麻烦事’?他知道多少?
我推道:“孩儿不知父亲在说什么……”
杜构冷冷看着我,满脸不屑,哼了声,道:“到如今你还不想说?好,我问你,年前你一夜未回,是不是被人追杀?和前几日那两人是不是同一伙?你查了这么久,可查出是谁想杀你了?”
我如雷劈中,他竟然什么都知道,我一直以为自己瞒的很好,没想到……是谁全告诉他的?杜安知道最多,难道是杜安?不对,杜安不知道我那会一夜未归发生了什么事……
我弱声回道:“没有线索……”隔了这么多天,我也想知道是谁,谁想每天出门都觉得被人暗地盯着,可一点线索都没有,又能怎么办?
“连关乎自己性命的事都处理不好,与三岁小儿有何区别?”杜构嘲讽道
我忍着,任他讥讽。杜构一定是暗地里派人盯着我,那人将所有的事都告诉了他,所以他才能知道我被追杀,然后派人查到了年前那次。
我道:“孩儿会查出来的,不过是时间问题”
杜构道:“好,我给你时间,随你去查,且看你何时查得出来”
……
闷了一肚子气出了书房。话是好说出去,可真要查,从哪查?我只知有人要我命,但又不知是什么时候树的仇人?只知道有两杀手,可长安上百万的人,找两个人完全大海捞针。
翌日,找孙禄堂派了活,回家等了几日孙禄堂就做好了。上回之后孙禄堂派人做了几种新图样,随意找了个合适的替太子做了。我领了戚大五人,给太子安置好了。
宫里暂时没了活,孙禄堂那里却忙地热火朝天,天气一天天回暖,下单子的人却一天天增多,好奇,问了孙禄堂才知道怎么回事。
原来是孙禄堂营销做得好,对客人做了心理工作。孙禄堂是这样讲的:这炉子,虽说是安好等天冷的时候用的,现在天是快过春,但那冬又不是不来了,暑来寒往,就一眨眼的功夫。有客人还犹豫的,孙禄堂就告诉伙计说,铺里的单子已经排到快九月了,非要等冬,可就来不及了。
我被孙禄堂的智(gui)慧(ji)深深折服。
到了上元节,闲暇时与苏宝同、萧守规聚了一面,我去的时候里面已经坐了三人,还有吕奕晨。
我起话头问道:“吕兄好像不是长安人吧?过年不回去吗?”
吕奕晨道:“在下扬州人士,家里双亲只剩阿娘,已经随我牵来长安住了”
我不好意思道:“三全唐突,但愿没冒犯了吕兄”
吕奕晨笑笑,道:“无妨”
“长安天气不同于淮南道,但愿吕兄住的还适应,没生离开的念头”
吕奕晨扬了下嘴角,像是自语道:“对我而言,哪里都是一样,只不过,她在长安”
我看了眼吕奕晨,只觉他是想到了什么人,看他神情,这人不像是他阿娘。
我又同萧守规聊了下最近发生的事,期间苏宝同只偶尔说两句,不时神游走了,不知自除夕那夜后,他发生了什么事。
谢绝了三人上元夜同游的邀请,我回了府。在没弄清敌人是谁前,我还是小心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