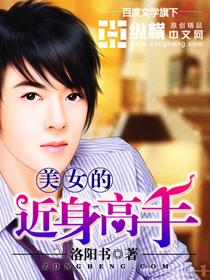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福喜多插座质量怎么样 > 第九十三章(第2页)
第九十三章(第2页)
起头是一位监察御史参奏吏部一名官员收受贿赂,私下更改官员考绩。
这件事说大不大,因为吏部那名官员就是个底层的笔吏,能够接触到的考绩也都是六品以下的官员。
但是说小却也不小,毕竟吏部掌管着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事务,一个弄不好污了吏部的名声,却也不是闹着玩儿的。
官家下令彻查此事的时候,陈太后也并未觉得有何不妥,但是接下来事情就渐渐失控了。
吏部作为六部之守,掌管的还是涉及全国官员的大事,他一个区区笔吏若是无人帮忙,如何能做到欺上瞒下,随意更改考绩?
于是经办官员顺着这名笔吏的线头一扯,顿时牵出另外三名吏部的官员,职位最高的是个正五品的职官——吏部司郎中杨清德。
这个时候陈太后就已经预感有些不好了,杨清德虽然名字看起来又清又德的,其实早就被陈家买通,这几年一直在帮陈家在朝中和地方的位置上安插陈家的亲信或是向陈家示好的官员。
果不其然,随着调查的深入,杨清德插手过的官员档案全被翻了出来,五年内的档案被一份份地核对查证,最后挑出有重大改动或是瞒报的居然有三十余人之多,其中有京官也有地方官,一时间朝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被查出来的官员中,陈家本家的亲眷就有十二人,其他沾亲带故的都算上足有二十三人。
陈太后在后宫急得团团转,但是在这个敏感的当口,那么多双眼睛都盯着后宫,她根本不敢传陈家人入宫,也不敢派亲信出宫送信。
在这件事的处理上,小皇帝根本没有过问陈太后的意见,直接让几个老臣拟旨,将这三十余人全部一撸到底,永不叙用。
这样的处置其实是有些冒险的,三十多个官员朝夕间被撸了官职,别说是如今幼主临朝,即便是朝局稳定之事都是十分冒险的事情。
小皇帝说要这样处置的时候,明显是堵着气说的,其实他心里也明白这样不好,但是因为心里实在太憋屈了,哪怕只能过过嘴瘾也想说个试试。
几位老臣自然都连连劝谏,可谁也没想到的是,沈闳居然对这个处置表示赞同。
众人都惊讶地看着沈闳,小皇帝看向他的眼神中却明显带了些连他自己可能都不清楚的希冀。
沈闳躬身道:“官家这样处置并无不妥,臣附议。”
小皇帝眸子瞬间闪闪发亮,也不管其余几位老臣依旧反对,小手一挥格外硬气地说:“诸位大人不必多言,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了。”
待到几位老臣告退之后,小皇帝又琢磨了半晌,才问沈闳:“沈先生,这样办真的妥当么?”
沈闳捋着胡子笑着说:“这样办的确是有点儿急进,但是把处置押后几日再公布,随后官家今年祭天的时候再下一道罪己诏,这件事便再无不妥了。”
“罪己诏?”小皇帝神色略微迷茫,前几个月天灾之时自己说要下罪己诏,沈先生明明说那并非天子的过错,此时为何却又让自己下罪己诏呢?
沈闳并未说话,而是静静地让小皇帝自己思考。
小皇帝想了半天,犹豫地开口道:“沈先生的意思是,天降之灾并非国君之过,重在灾后如何抚民。但朝中有官员欺上瞒下朕却未能及时明察,这才是朕之过错?”
沈闳欣慰地颔首,补充道:“官家说得没错,道理的确是这样的,但是黎民百姓并非人人懂得道理,所以才会有人以讹传讹,说天灾乃是君主不贤。但如今官家揪出这么多欺上瞒下的官员,却正好证明您是贤明之君,即便天灾当真是天降之罚,所惩罚的也并不是官家。”
小皇帝差点儿被沈闳这番话绕晕了,支着下巴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这意思不就是说——虽然天灾并非是因为朕年幼无德,但是架不住外面会有很多不懂事的人这样想这样说,如今抓到这些不法官员,顺势把天罚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这样一来可以对其严厉处罚,二来也能堵住外面的悠悠众口……
把沈闳不方便说出口的这些弯弯绕都想明白之后,小皇帝深深觉得自己又学了一手,看向沈闳的眼神也越发崇拜,情不自禁地感慨道:“沈先生果真是满腹妙计,朕受益良多,今后还请先生不吝赐教。”
陈太后几年间费心费力安插的人选,一朝之间几乎被拔除殆尽,面子里子都丢了个干净,选后之事也不敢再提,开始信佛抄经,开始只是做做样子,后来抄的多了,心倒是静下来了不少,一时间前朝后宫相安无事,格外和谐。
说话间就已经是腊月二十了,京城终于下了今年的头雪,而往年极少下雪的沂南也从早晨开始飘起细碎的雪花,越下越大,到中午的时候已经是鹅毛大雪。
小黑乐得在屋里直蹦高,爪子搭在窗沿上,鼻子湿漉漉地贴在窗纸上,顿时就捅开个窟窿,它自觉做错了事,赶紧扭头去看沈福喜的神色,见小主人并没有责怪,反倒是笑得开心的模样,顿时又扭过头去一使劲儿,大半个脑袋都拱到了窗外,雪花落在鼻尖上,瞬间融化成沁凉的雪水,让它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喷嚏。
赵氏听到动静回头一看,小黑的脑袋已经钻到窗外去了,窗纸破了老大个窟窿,但是因为有它堵着所以倒是没有冷风灌进来。
再看女儿在一旁笑得欢实,根本没有阻止的意思,忍不住嗔怪道:“你赶紧带它回你自个儿房里去折腾,别在我这儿祸害东西。”
沈福喜揉着小黑的后颈道:“它去年等了一冬都没等到雪,失落了好一阵子呢,今年好不容易下雪了,还不让它乐呵乐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