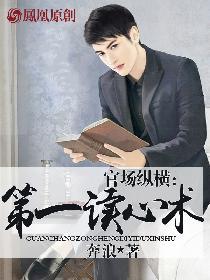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一章概括 > 第2章(第3页)
第2章(第3页)
克利姆卡吓得一哆嗦:“真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保尔回答。这时,门开了,格拉莎睡眼朦胧地走进洗碗间。
“小家伙儿,你们怎么都不睡?火车还未到时,睡上一个钟头。去吧,保夫卡,我替你的班。”
保尔丢掉这份工作,比他自己预料的还早。原因更是出乎自己的意料之外。
一月里寒风刺骨。保尔干完活儿赶着回家,但接班的还不来,保尔找老板娘,说要回去,可老板娘死活不放。已精疲力尽的他,只得接着干第二个一天一夜。天黑时,他实在累透了。在稍稍安静的一段时间,他还得赶在三点钟火车进站前灌满几锅水,然后烧开。
保尔拧开龙头却没水往外流。估摸是水塔坏了。他让龙头开着,想横倒在柴堆上歇歇气。不过他抵不过睡意,睡着了。
过了几分钟,龙头响了,水流出来,漫了水槽,不多时便顺着瓷砖流向洗碗间地板。洗碗间如往常一样没人,水越积越多,从门底朝大堂流泻。
旅客们都在熟睡。一股股水流悄悄流到他们的包和箱子下面,但没有一个人发觉。直到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给泡醒,猛地跳起来又叫又嚷时,人们才慌忙扑向各自的行李。顷刻间,人们乱作一团。
水却依然流个不停,积水更多。
正在另一个大堂收拾桌子的普罗霍尔,听到嘈杂声,踩着积水跑到门口,用力把门撞开。而原本被挡住的水,“哗”一下全涌进了大堂。
叫嚷声更高了。几个当班的伙计跑进洗碗间。普罗霍尔猛地扑向熟睡的保尔。这男孩接着便被一阵猛揍。
但他睡意依旧,惊醒时什么也不明白。不过感到眼冒金星,头晕目眩,浑身都疼。
他拖着疼痛的身子勉强一瘸一拐地回家了。
清早,阿尔焦姆皱紧了眉头,听保尔讲整件事的原尾。
“是谁打了你?”“普罗霍尔。”
“好,你躺着吧!”阿尔焦姆用低沉的嗓音说。然后披上羊皮袄,闷着头走出去了。
“我能找一下普罗霍尔吗?”一个陌生的工人问格拉莎。
“他就来,你等等吧。”格拉莎回答。
这工人将自己宽大的身子靠在门框上。
这时,普罗霍尔端着一大堆杯盘刀叉,一脚踢开大门走进洗碗间。
格拉莎说:“嗯,这就是普罗霍尔。”
阿尔焦姆一步跨上去,用力按住这个伙计的肩胛骨,怒视着他问:“凭什么打我弟弟保夫卡?”普罗霍尔想挣扎着脱开身,但已被一记重拳打倒在地。正想站起来,一记更有力的拳头让他趴下后动弹不得。
洗碗的女工都吓得纷纷闪避。
阿尔焦姆转身往外走了。普罗霍尔在地上不停地抽搐,满脸鲜血。
当晚,阿尔焦姆没有回家。母亲打听到的消息是:他被宪兵队抓去了。
六天后的晚上,他回来了。母亲已经睡下,阿尔焦姆径直走近坐在床上的保尔面前亲切地问:“弟弟,好些了吗?”“没事!”他一边坐了下来一边说:“还有比这倒霉的呢。”稍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没事儿,你到发电厂干吧。我给你讲好了,那儿可以学些手艺。”
保尔紧紧抓住哥哥那双结实的大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