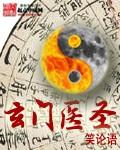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妇女工作日记怎么做 > 第九十一章 岁月如歌(第2页)
第九十一章 岁月如歌(第2页)
昨下午因一男孩被水淹死,他们老师轮流看守尸体。
今早,沈来了我门市部,坐在那里翻书看。别的人老问他,那孩子是怎么死的?他刚一进来时我也问过他,随后也就不想谈,全是别人在好奇的返来复去的问他。
人就是这么悲哀,没死时,把生命看得很轻,等死了,才知道珍惜。
而同样是死了一个人,他的家人会痛不欲生,别人只能为他哀叹几句,过后一定成新闻来谈论。
人一生的终结就是“死”,结束了所有的快乐痛苦,象睡着了不会再醒的安息样子。只苦了活着的亲人,一百个不愿意不舍和痛苦,走的人自由飞到他想要去的地方,活着爱他的人会有多痛心?
我也想去看看那孩子的,他说:“你不怕呀?”
我也玩笑说:“韩燕这样想死又不知怎么死才不痛苦?”(很多年以后,我怎么也不相信,玩笑的话会成真?现实怎么这样残酷?)
其实死真的很容易,一条河流,多么温柔舒服,把你诱惑下水,只那么几分钟,就把你活活淹没,似游戏般的戏弄你,不知不觉的吞淹了你。
女人是水,她给了你生命,却又在酷暑中吞噬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
我们说起了“画”。
他说:“这就明白什么是似与不似了吧?”
我说:“似是媚俗,”
他接着说:“不似是欺世”,好象我们很有默契很有共同的兴趣一样。
我说:“上次我说你画的画冷傲孤僻如你的性格也没错吧?”
他自己也笑笑说:“八大山人什么伤心鸟”,“荷叶也有残荷”。
看见班车来他就走了,问他什么也走神不知在想些什么?我是否在试着去了解他?了解得越清,就越失去了幻想的美好。
九o年六月二十三日晴转阴
早上下班洗了纹帐,下午打雷下雨,又闷。
现在的心情,也不想和文友同学通信了,也不大关心哪个男孩追求哪个女子,笑一笑,什么也不想说。真正是一点也不希望有人来“缠”我,反倒害怕他们来,浪费我的时间。
写作上也不刻意,热切的与人交流,投稿呢,也放在那里长时间不去寄,冷在一旁。是我意志消沉?还是失意太多?有时候什么不要都可以,为什么还要苦苦追求?在乎得不到的而去苛求自己?折磨痛苦自己?
我只是要做我自己,只是想到了终点又回到起点,这样日复一日的做着自己想做的事,不是很快活吗?
不过眼前的事又不是不放在心上的,比如那个小燕子,她回去几天了,我乐得清静,但她久不回来,我还是等着她回来,好倾诉心中的一点快乐和悲伤。吵一吵,闹一闹,也挺开心的。
不过等她真的嫁人失去了她,我的生活会不会就此还有快乐?
小燕子在中午回来了。
晚上洗完澡我们穿着短装长裙去散步。
她的那套裙子圆点点的好美,我的是一套淡青色,两人一起在深圳蛇口街买布料做的裙子,穿起来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我们说,在一起以后,两人都变了。她说她变得开朗,好玩,说之前常面无表情的。我说我变得爱漂亮,爱打扮自己爱斯文了。
我们仍慢步于去中学那条马路,顺便去别的老师那里看看,想不到一下子就凑合了六个人,四副扑克牌。玩的时候我也不是太认真,所以也没有以前激烈,在乎,争强好胜的小孩子一样的天真了。
我平和,恬静,不再去与人争执什么,他们说什么肥婆我也一笑置之。玩完了就走了,心里竟然不牵挂他。
可惜走到桥头因没人相送,我们折转回来,求那个炒菜厨师要一起走,可他们还不尽兴不肯走,我们只能等,我等得不耐烦也不喜欢这样聊下去,好想快点回到我宁静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