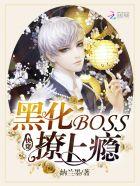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就是妖怪小绿真实身份 > 第161页(第1页)
第161页(第1页)
阿破挺了挺身子道:“有水吗,我渴了。”两个白大褂一边费力地往下抬担架一边说:“别给他多喝,这是失血过多的症状。”阿破坐起身接过我递过去的一瓶水,见两个人抬得辛苦,边喝边说:“我自己走吧?”袁静按着他肩膀道:“你别动,快躺下。”然后又对我们说,“你们去办住院手续,我陪他进去。”两个男护抬着担架飞快地跑上台阶,阿破在担架上兀自说:“住院?我可不干,随便挂个科瞅瞅就行了……”说着趁担架路过垃圾筒把手里的空瓶子投在里头……小慧跺脚道:“无双去交钱,我和阿忆去看着他。”这时候已经是夜里将近12点,医院里已经没什么人,通往三楼急诊室的电梯正在检修,两个护工只能抬着担架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跑,刚跑到2楼中间,其中一个已经上气不接下气,老史把他推在一边,自己抬起担架,阿破吓了一跳,噌一下跳到地上,在两个护工的目瞪口呆中道胁肩谄笑道:“怎么能让您受累呢,我还是自己走吧。”小慧吃了一惊,作势扶住阿破,阿破道:“我自己能行。”小慧语气里暗含威胁道:“真的行吗?”我在旁边一个劲给阿破使眼色,阿破随即恍然,一个趔趄道:“就是有点晕。”袁静道:“你们扶他慢慢上去,我去找医生!”说着先跑上楼去,阿破在我和小慧的搀扶下装模做样地一步一摇,在过道里跟我咬耳朵:“这样行吗?”我小声告诉他“脚再拖点地——”三楼的值班室里却只有一个小护士,看样子还是刚实习,她一见阿破浑身是血顿时吓得六神无主,捂着嘴全不知道该干什么了,只会一个劲说:“你坚持一下,你坚持一下,医生一会就来。”袁静和老史一起冲她吼:“医生哪去了?”小护士慌张道:“有个老太太从楼梯上摔下来,也是急诊。”阿破找了张凳子拍拍坐下,安慰她道:“你让他别急,千万把老太太安顿好了,我等等就等等。”袁静愣了阿破一眼:“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她抓住护士的胳膊道,“你看看这个人,他刚才在路上已经流了很多血,再耽误几分钟很可能就有生命危险……”“我去找医生。”小护士噔噔噔跑掉了。袁静关切地问阿破:“你感觉怎么样?”我小声提示阿破:“虚弱。”阿破立刻四仰八叉地躺在凳子上,幽怨道:“我很晕……”袁静看看表焦急道:“这医院怎么回事?”这时一个50来岁的老大夫终于在小护士的陪同下急匆匆出现在走廊里,脖子里还挂着听诊器,小护士一边走一边语无伦次地跟他介绍阿破的病情,老大夫来到我们跟前,皱眉道:“病人呢?”阿破忙举手道:“我就是。”老大夫只打了一眼阿破身上的血,立刻就急了,训斥小护士道:“这么危重的病人怎么不赶紧抢救?”小护士讷讷道:“可是我……”老大夫严厉道:“你们护士长呢?就算我不在,挂水验血这些事情你也不会吗?”阿破道:“你别为难她了,是我说等等的。”老大夫听了这句话重新打量了阿破一眼,奇怪道:“你好象伤也不重啊。”阿破咧嘴笑道:“本来就……”我一拍他,阿破只好道,“呃,反正也不轻。”老大夫走过来拿住阿破的手腕,又翻开他眼睑看了看,自言自语道:“不可能啊,流了这么多血还这么精神?”他见边上有警察,遂问袁静,“警察同志,什么情况?”“械斗。”(塞班论坛忘塵居士整理制作)老大夫吓了一跳,袁静随即解释道:“别害怕,他只是受害者。”“哦。”老大夫这才放了心,吩咐小护士:“去把你们值班护士长叫来,我要给病人做个全面检查,还有,让血库准备一下,我随时要用血……”“别呀!”阿破顿时叫起来:“哪用那么麻烦,我这就是点外伤。”上回陪叶卡捷琳娜住院学的词今天算用上了。大夫冷冷道:“脑袋掉了也是外伤,那就不用麻烦了。”阿破一把拉住大夫,讨好道:“商量商量,您给我随便包包,我还想赶紧出院呢。”大夫夸张道:“你都成这样了还想今天出院?”袁静道:“听大夫的。”我给小慧递个眼色,小慧无奈道:“大夫,要不这样吧,您先给他做个大致的检查再做决定。”我和她都明白,以阿破这种性格待在医院里是非露馅不可,而且时间越长越危险,不如找个借口先回去再说。大夫想了想,只能同意,他指指阿破道:“你自己能走吧?跟我进来。”老史道:“小子,可别逞能啊!”“我陪他进去。”我假意扶着阿破说。小慧趁我们进门的工夫嘱咐我和阿破道:“一会千万别演砸了,阿破,你要看阿忆的提示!”事到如今,不说老史,总得给袁静一个合理的解释,她眼睁睁看着阿破被砍成血葫芦,可在救护车上躺了一会就又活蹦乱跳的了,这显然说不通,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会正中元妖下怀——他的目的就是让人类发现我们的真实身份。可是话说回来,让阿破装做弥留之际躺在手术台上让他们抢救这更不现实,所以现在扭转局面只能是靠一个“演”字,我们两个得唱出双簧,我在后面说,他在前面做。那老大夫把我们带进一间诊断室,戴上橡胶手套,对阿破说:“把衣服脱了。”阿破随手一扯,本来就被砍成碎布条的上衣便脱落下来,露出七横八竖的伤口,因为没有特意用妖力治愈,有的还在汩汩冒血。大夫看了一眼那些伤口,感慨问:“当时多少人在砍你?”“二三十个吧。”“哦,他们为什么砍你呀?”“……不知道,可能看我老实吧。”“你老不老实我不知道,但你一定是个很迟钝的人——你没感觉到疼吗?”这时我们才发现大夫已经用蘸着酒精的棉签帮阿破清理出一条伤口,如果是一般人,这会恐怕早就疼得骂娘了,可阿破还稳稳坐在那里跟人聊天。此时此景,大夫看看阿破,阿破看看我,我又看看大夫,大家似乎都在等着对方解释,急中生智的我一拍阿破道:“你是疼迷煳了吧?”阿破听我说完又迟钝了一秒,急忙调整表情,惨叫道:“啊——”“其实也没那么疼吧?这伤口都快结疤了,而且这是我特地发明的谈话疗法,目的就是转移伤者的注意力,效果还不错吧?”我们都赔笑:“不错,不错。”阿破小声嘀咕:“你他妈玩死我得了!”这时,老大夫忽然扶了扶眼镜,瞧着阿破肚子上一道伤口惊讶道:“这刀捅得够深的啊,肯定有内伤了。”阿破低头看看道:“内伤怎么了?”“内伤就得马上动手术,而且得住院。”大夫不住地小心擦拭伤口,只见那伤口皮肉外翻,里面不知道有多深,大夫用完一瓶酒精棉,返身去取,我小声责问阿破道:“不是让你把肚子上的伤口弄好吗?”阿破无辜道:“当时你们说了那么多,我哪能顾上一个不落啊?”“现在怎么办?”“好办——”阿破说着双手平举,控制着妖力把肚子上的伤口平复成一条小刀口,然后抬头问我:“看不出来跟刚才不一样吧?”我抓狂道:“瞎子都能看出来!刚才光口子就这么长——”我在他肚子上比划着,阿破二话不说拿起桌上的手术刀照我的手势又拉了一下,趁大夫回头赶紧放下。大夫刚坐下立刻就发现阿破那道伤口不一样了,他睁大眼睛道:“咦,刚才明明是刺伤现在再看倒像是刮伤了——”他把眼镜拿下来使劲擦着,喃喃道,“难道是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