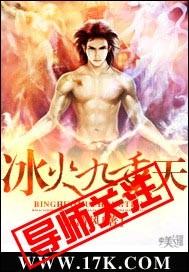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掌上娇卿讲的什么 > 第95章晋江正版95(第2页)
第95章晋江正版95(第2页)
那一脚不会让他五脏俱裂,但也绝不会让他好受,后来那顿鞭子,说是毫无私心也不可能,只能保证他不死罢了。
谢危楼看着她澄澈的眼睛,心中的怒意早就散了,“这就叫教训你了?”
沈嫣轻轻“嗯”了声,抬头看他。
谢危楼无奈笑了下,身子低下来,额头贴着她额头,“那你说,怎么罚我?”
肌肤相贴,沈嫣眼睛一烫。
这么好的机会,不狮子大开口一次都觉得吃亏,她眨了眨眼道:“往后除非人前,否则不许拿镇北王的身份压我。”
谢危楼蹙眉:“我有过吗?”
沈嫣不管,继续道:“不许倚老卖老,仗着比我年长,处处凶我、教训我。”
谢危楼脸色发黑:“嗯。”
沈嫣说到第三点,将被他攥红的手腕怼到他眼前:“不许仗着力气比我大,压制我、欺负我,我反抗不过,只能遭殃,就罚你……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不许你的力气比我大!”
谢危楼忍不住笑,接过她伸来的手腕,在那红印子上吻了吻。
姑娘家皮肤太过娇嫩,还没怎么碰,就捏出了印子,不过消得也快,他才吹了下,就消去了大半。
谢危楼抬起她下巴,在那一张一合的唇瓣上摩挲了下,“前两点可以保证,至于第三点么,是不是太无理取闹了?”
沈嫣抿抿唇,软绵绵地说了一句:“我活了两辈子,也只能对你一个人无理取闹了。”
这话说出来有种伤感的味道,谢危楼仿若心口塌陷下去一块,酥酥麻麻的质感传遍四肢百骸。
他叹口气,将人拢在怀中抱紧,嘴唇吻在她鬓角,“我只能答应,不拿力气来欺负你,宠你、疼你、保护你不能算进去。”
沈嫣想了想,点点头:“勉强可以吧。”
她忽然想起什么来,缓缓松开他:“谢斐……真的是玉嬷嬷和玄尘大师的儿子,不会有错吧?”
谢危楼道:“倘若不是证据确凿,我也不会怀疑到玄尘头上。”
沈嫣有些担心皇帝跟前难以交代,“你将他带到京城抚养二十年,今日才真相大白,陛下会不会治你个失察或治下不严之罪?”
谢危楼听到这句,倒是松了口气,原来她关心的不是谢斐,而是担心皇帝会不会为难他。
他一笑:“治罪定然是要治的,不过不会太重。”
沈嫣紧张地看向他:“你怎么知道?”
谢危楼带着她继续往老太太的院子去,一边同她解释:“此事大长公主才是幕后主使,某种程度上,我倒算得上是个受害者,陛下若想罚我三分,必罚大长公主七分,大长公主可是他亲姑母。”
他想了想,皇位倾轧复杂,不宜对她说得太多,便只道:“便是治罪,不过是些无关痛痒的罪名,放心吧。”
沈嫣一想起坤宁宫的紫云香,对皇帝总是多了几分畏惧,一路上忧心忡忡,转眼就到了老太太的厢房外。
她疾行两步向前,将两人并肩同行掩饰成她在前“带路”。
含桃在外守着,见沈嫣与镇北王过来,连忙上前行礼。
沈嫣道:“王爷来看祖母,你去通传一声吧。”
含桃立即应声进去了。
后山厢房出事的时候,暗卫包围了整座后山,不准任何人进出,为防毒烟扩散,让所有香客轩窗闭紧不得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