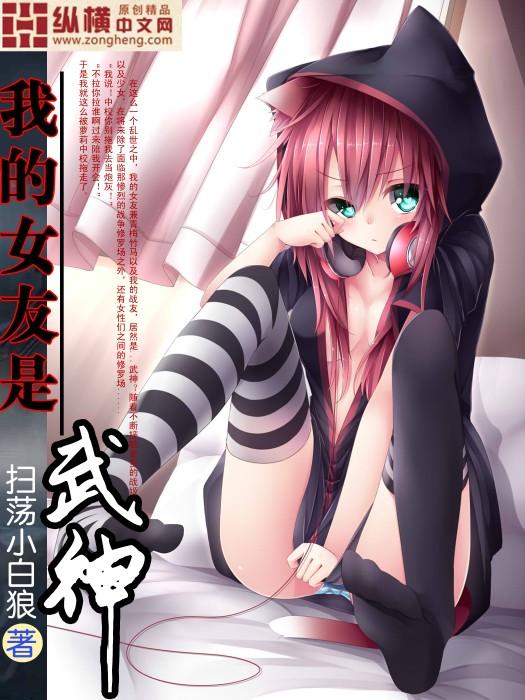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农家小调炊饭香 第1章 > 第八十二章 别再糟践老娘的东西了(第1页)
第八十二章 别再糟践老娘的东西了(第1页)
沈氏正在数落她这个大儿媳的不是,说她以前以要带娃子为由,偷懒耍滑不干活,一条条指的是清清楚楚。
原本沈氏是挤兑秀娘的,可一说起文氏她也气恼地很,她这边说得痛快,文氏在屋里可听不下去了。
她裹了件外衣就出了堂屋,“吵死了都,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沈氏瞪了她一眼,见她护着肚子,想骂的话又给憋了回去,黑着脸道,“大清早天凉的哩,你出来干啥,仔细我孙子。”
文氏冷笑一声,不温不火说道,“婆婆,你也知道是这会儿是大清早啊,你吵到你孙子不要紧,你要是吵到旁人,保不齐得个骂名。”
沈氏这一早上,合着想发火都发不出了,她不耐道,“得得得了,就你知道的多,回去睡你的觉去!”
文氏得意的看了沈氏一眼,喊了楚老爹一声儿,拽着衣裳裹紧身子,扭头就回屋去了。
楚福忙道,“娘,你别生气,娟儿就这样,她、她怀着娃,让吵醒了火气就上来了,你别在意。”
沈氏伸手打了楚福一下,“得了,就你会护着你媳妇儿,她早起了不舒坦,你老娘我就活该受苦啊,老娘我也不舒坦!”
秀娘在里屋听了一笑,这真是一物降一物啊,文氏这样的软磨性子,倒是可以压得住沈氏那火爆脾气。
她梳好头盘起发髻,走到床边的大木箱子前,那上面有个盛满水的陶罐,边上放着一个装满咸盐的小碟子。
起床后只是漱口还是不咋样,秀娘便用手指蘸了些盐抹到嘴里,来回搓一搓,再从陶罐里舀水出来漱漱口就得了。
早先楚戈出去后她就起床了,昨个儿她先舀了盆水放在屋里,因为下阳村夜里阴冷,缸里的水在院里晾了一宿,到了早上冰的钻牙,所以秀娘才舀了水进屋放着,早起用着刚刚好。
洗漱完整理好床铺,秀娘穿好衣裳就出去了,等她到了院外,沈氏还在数落楚福,楚戈则进了灶里,估摸着是蘸咸盐漱口去了。
前阵子秀娘可是花了不少功夫,才叫楚戈兄妹三个早晚蘸盐洗牙的。
秀娘走过去与楚老爹打了声招呼,楚老爹一早听了沈氏唠叨的,瞅着儿媳妇睡得这么晚才起来,心里多少有些不高兴,他只淡淡的应了一声。
沈氏斜了秀娘一眼,清了清嗓子,秀娘依旧没有吭声,楚老爹皱了皱眉,拽了沈氏一下。
昨儿他就跟这老婆子说了,她不是还没叫老二家的么,这就是没承认她,那老二家的哪能先开口啊!
沈氏知道自个儿老伴的意思,她不情愿的抿了抿嘴,“老二家的,你咋这么晚才起来哩。”
秀娘看着她一笑,“婆婆早,昨儿赏月晚了些,这才睡迟了。”
沈氏还是沉着脸,“既然起来了,赶紧的吧,起灶做饭去。”
大清早起来秀娘也不想生一肚子闲气,她应了一声,挽起袖子往灶间走,反正她和楚戈也得吃饭么,无非就是多要几碗水下去煮么。
秀娘到灶里淘米下锅,楚戈拿了个盆子,正要舀水洗脸,秀娘让他到屋里,说她洗漱用的水还有,让他到屋里洗漱去,顺便换身衣裳。
沈氏听到了不咸不淡的嘀咕了一句,“老二家的,合着你还搁屋里洗脸漱口哩,真娘咧矫情。”
秀娘笑道,“是哩,起来了不漱口,我可受不了那味,这不就得赶紧漱牙口么,要不可就熏人了。”
沈氏愣了下,没话说了,她不自在的伸手挡在自个儿嘴前,在二叔公家,她连灶房朝哪开都不知道,更别说寻水漱口了。
楚老爹则蹲到外头抽旱烟去了。
秀娘舀了水回到灶里,从灶台上取了火折子,瞧着灶里的柴禾没有了,估摸着是楚老大昨个儿用完了,她便又出了灶间。
可出来了她却瞧见原本灶门口堆放柴禾的地方现在空空的,连一根都不剩的。
秀娘觉得奇怪,前天晌午楚戈还上山砍了柴回来,加上前阵子的还得有三四捆哩,咋才一宿就没了呢。
昨个儿就算楚福再怎么可劲儿的烧,那也烧不了这三四捆子柴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