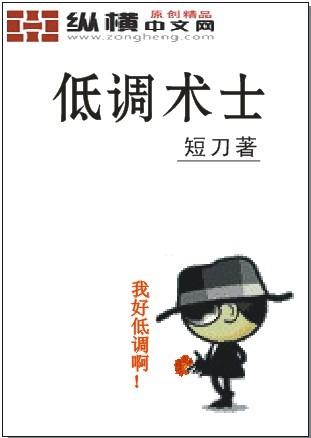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红楼蕴大爷无防盗 > 第一百三十章宁王的心思(第1页)
第一百三十章宁王的心思(第1页)
皇城,大明宫。
这才不到九月,秋叶尚未落尽,然而大明宫内,却已经烧起了地龙。
宫人和侍卫们,行走处,额头多可见汗。
富丽堂皇的大殿内,一老一少两个人坐在殿内,中间摆着红楸木棋盘,显然两人正在对弈。
年长者满面须白,脸色蜡黄,然自身却有一股睥睨天下的气势,此人正是太上皇赵贽,而与他对弈之人正是其幼子,大乾朝的宁王。
太上皇右手执白玉精做的白棋,看着面前的宁王久久尚未落子,和善地说道:“熙儿,今日你怎么心不在焉的,往日下棋可没这般优柔寡断。”
宁王面露苦涩,恭敬回道:“父皇,儿臣近日公务繁忙,故此心思不定,还请父皇莫要见怪。”
太上皇闻言皱了皱眉,关心地问道:“你不是在礼部吗,非年非节,怎会忙碌起来?”
宁王眼神一凝,心中窃喜,不过神色不变,回道:“父皇,前几日,宁国公府的贾珍没了,现今承袭宁国公府的是贾蕴,父皇也知晓贾府乃是世之国戚,礼部自然不能怠慢。”
大乾朝的爵位考封虽是宗人府在管,可最终还是要经过礼部核实,册封玉牒之类的也需要重新制作,所以礼部也闲不下来。
太上皇闻言眉头一皱,沉吟片刻,询问道:“贾蕴?可是那个拱卫司的贾蕴?他不是过房到宁国公府的旁支了,怎会轮到他承爵,简直是胡闹。”
宁王一本正经的回道:“父皇,那宁国公府长房无人,而贾蕴本就是宁府长房庶长子,重新过房倒也正常。”
太上皇皱了皱眉,开口道:“记得你说过贾蕴好像是被除了宗籍?”
宁王闻言回道:“贾蕴确实被除了宗籍,不过贾府又让贾蕴认祖归宗,承袭爵位,若不是如此,儿臣也不需这般辛苦。”
因为贾府的一番骚操作,为礼部增添了不少麻烦事。
太上皇闻言顿时脸色难看起来,不满道:“这国公府家大业大,难道连个承爵的人都寻不出来,非得惹出笑话?”
宁王闻言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太上皇见状皱眉道:“有什么直说便是。”
宁王面色为难,沉吟片刻回道:“父皇,宁国公府贾珍本有一嫡子,名为贾蓉,不过贾珍之死与其有关,故而已经下狱,不日便会被流放,故而宁府无人承袭。
皇兄因此事大发雷霆,本想褫夺了宁府的爵位,幸得祖母求情,故而法外开恩,不过却言明贾珍若无子嗣不得承爵,贾府也是没办法才让贾蕴认祖归宗,承袭爵位。”
“混账,这等忤逆不孝之人焉能开恩,简直不知所谓,也只有那混账做的出来,一个德行的人。”太上皇开口叱骂道,至于骂谁,宁王心中有数。
太上皇闻言抬眼看了看宁王,心中已经明白了过来,敢情贾蕴袭爵是崇明帝的意思。
众所周知,拱卫司是天子近卫,自然非心腹之人不可掌管,故而贾蕴本就是崇明帝的人。
沉吟片刻,太上皇开口道:“罢了,子承父爵,倒也挑不出毛病。”
宁王闻言心中一愣,没想到太上皇如此容易便接受下来,难道不晓得贾蕴袭爵代表了什么意思?
贾蕴袭爵,其意昭然若揭,贾府乃是军中之首,近年来虽是落寞,可对于军中的影响力却是不少。
不仅如此,京中勋贵大多以贾家为首,如今天子心腹承袭宁府爵位,同时亦是贾族族长,那不代表贾府已经投靠了崇明帝。
京中勋贵虽是亲近太上皇,可太上皇身体却不怎么乐观,已经常年不理宫外之事,这般情形,有不少勋贵态度愈发的模棱两可。
贾蕴承爵,难免引发其他人的心思,毕竟这些勋贵也只是为了家族利益,有贾蕴在前,他们也不得不仔细思量,这对于宁王来说可不是好事。
太上皇瞧出了宁王的不安,开口道:“贾蕴不过一黄口小儿,承担不起国公府的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