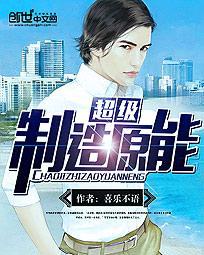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一人一世黑白影画 > 第二十五章 相思赋予谁2(第2页)
第二十五章 相思赋予谁2(第2页)
她既然敢提这种要求,他要是个男人就不会再拒绝。
程牧云打横抱起她,从水泥台上跳下来,进门,上了三楼。
那个小房间,他刚才进去看到那张床的时候就想把她丢上去,现在,既然她都这么要求了,他怎么可能不去做?
印度的这种棉布,在他手里根本就和纸一样,稍用力就撕裂开。温寒吃不住他的力气,咬上他的肩,把他整整两日让自己低落的情绪全部都狠狠还给他。
他低声笑,用俄语低声耳语了句:再用力点,宝贝儿。
……
有人出生几个小时*就冰冷了,有人活了上百年最后的心愿也不过想要无疾病痛苦的善终,有人结婚前夜怀揣百年好合的梦遭遇意外,有人千帆过尽爱人都成灰了自己却还在——
人之出世,如优昙钵花,时一现耳。
分得清、辨得明,
今时今日,此时此刻最渴望的是什么就够了。
深夜,那几个祭司回来。
温寒脸色红润地捧着个水杯,坐在电视机前看英语节目。程牧云切了一盘子水果端出来,丢在矮桌上。
两个跟着程牧云的女孩子们都比较避讳,去了旅馆住,倒是这个妹妹跟着他今晚暂时住在这里。对着三个印度年轻男人献殷勤,温寒起初不太习惯。“在印度,是有不能喝酒的dryday的,”年轻人热情地告诉她,“无酒日,还有不能喝酒的邦区。”
“是吗?这种法令在莫斯科一定行不通,那是个无酒不欢的城市。”她回答。
年轻人立刻笑:“但你要相信,我思想没那么死板。”
温寒被这个年轻男人的热情搞得很尴尬:“我相信……”她看了看身边的程牧云。想到他告诉自己要配合扮演兄妹,因为如果她是程牧云的家人,将会得到更多的、更有利的保护。毕竟印度这个国度,对女朋友或是妻子的在意程度实在不敢恭维。
幸好,这只是一种很热情而又礼貌的表达好感的方式。这些男人是婆罗门的,连别的种姓都很少通婚,更别说和个外籍人。他们察觉到温寒实在没什么兴趣,而又,碍于她“哥哥”在身边,也不好太过大献殷勤,话题很快转了开。
然而他们完全听不懂,程牧云时不时冒出的一句俄语,却比他们更要露骨得多。
比如,现在,就出现了如下对话。
“恭喜你,”程牧云手搭在靠垫上,低声说,“你又开始让男人为你神魂颠倒了,我甚至要开始怀疑是不是一直中了你的*计。”温寒就坐在他身边,但保持着成年兄妹该有的“安全”距离,也用俄语轻声回:“明明第一次是你认错了人……”
“你真这么以为?”他喝了口矿泉水。
“不是吗?”
“不是。”
“……”
“我在雪域高原就为你神魂颠倒,在尼泊尔再见到你,只觉得是佛祖显灵,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下半身,就随便找了个借口拉你进房间,非礼你,”他低声笑,“你看,亲爱的,这个回答还满意吗?”
她咬着自己的下唇角,开始学会和他你来我往:“嗯,还不错。”
明知道是假话,可又何必计较真假。好像过了刚才在房间里的那独处的两个多小时,两个人之间有什么被打破了。
“看来,我不止撕掉你的衣服,还撕掉了你不太可爱的一面。”他举了举手中的玻璃杯,小动作是,隔着衬衫摸了摸自己被咬得那块地方。她脸热,忍不住踢他。
“你和你妹妹感情真好。”身边人用英语表达羡慕。
“一贯如此。她喜欢偶尔和我斗嘴,试图挑战我作为兄长的权威。但我更喜欢谦让她,随便她胡闹。”他也用英语回答,表现的就是个合格的哥哥,丝毫不介意这些男人对她的追求。
而就在十五分钟前,在房间里,他还将满是汗水的脸低下来,去亲吻她的肩峰。
***************************
她有多久没好好睡一觉了?
从尼泊尔的那个小神庙开始,她就没好好睡过,火车上也是轻易就熬了一个通宵,再到这里。
温寒这一夜睡得格外沉,甚至在梦中,屡次推开自己的莫斯科家中的小木门,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对着自己,她低声用俄语叫他的名字,然而他一动不动,就是不回头。
耳后有湿漉漉的触感,把她从梦魇中拽出来。
她在半梦半醒中,仍沉浸在他不肯理会自己的伤情里,身上就已经有男人的重量压上:“早。”
“嗯……”她迷糊着。
她又“嗯”了声。
“有没有想过,要是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坏人?你怎么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