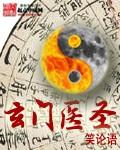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缄默成殇含义 > 第58章 伤疤(第1页)
第58章 伤疤(第1页)
红,刺眼的红。
闵关绍静静凝望着臂弯中女人的睡颜,大掌再次附上她的左手腕,却见她又一次躲开。
奇怪,一条丝巾而已,雪儿就这么在意?婚礼上不肯摘,睡着了都不让他碰。
闵关绍是个越挫越勇的人,还真来劲跟这条丝巾杠上了。
轻轻放开臂弯将女人的小脑袋安置在柔软的枕头上,惹来一声不满的嘤咛,他轻笑着吻了吻她的细唇以示安抚,然后视线来到她的左手腕。
小心翼翼的揪住丝巾一角,方一用力,只听——
啪!
一个耳光。
闵关绍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是她打他的第七个巴掌!他都记着呢!
气呼呼的用一只手按住她左胳膊不动,另一只手去解她的丝巾,孰料没等扯下来,女人突然剧烈的挣扎起来,那胡乱踢打的双腿和到处挥动的右手以及极度扭曲的五官,都像在忍受着什么巨大的痛苦,教人看得揪心。
“好好好,不碰了,我不碰了,睡吧,雪儿,我不碰你的丝巾,乖乖睡觉啊……”
闵关绍柔声呢喃着,以唇吻着她的,慢慢叫她平复下来,却是不肯罢休,嘴上吻着她,右手以一个巧妙而又不惊动她的动作缠上她的左手,十指相扣,将她轻轻的带到头顶位置。
慢慢的,女人在他怀里平静下来,闵关绍也不敢懈怠,继续吻着她,直到吻到偷偷解开了她的丝巾,直到确定她不会醒过来,这才罢休。
这女人,喜欢他的吻呢!
闵关绍为这一发现雀跃不已,然而下一秒他的雀跃完全僵在脸上。
抬头,但见一条狰狞的伤疤蜿蜒盘踞在雪白的皓腕,丑陋不堪,触目惊心。
轰——
那一刻,闵关绍完全失去反应,脑海中一直回旋着四个字:
割腕自尽!
割腕自尽……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心里还存有芥蒂,那么这一瞬,看到这条伤疤,他心中的郁结全都不翼而飞,变得豁然开朗,闵关绍想买醉算什么?厮混算什么?孽种又算什么?比起死亡,那些都算得了什么?
他寻寻觅觅找了七年,曾经他真的放弃过,迷茫过,也害怕过,害怕他的雪儿早已经不在人世,那么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如今他的雪儿就静静的躺在他身边,她喜欢他的吻,她会对着他脸红害羞,她还会跟他耍脾气闹委屈……
够了,真的够了,他不贪心,失而复得的喜悦没有人比他更能体会,他甚至想好了,他想说:“雪儿,如果你真的放不下那个孩子,那么我们就一起养育他吧,我会允许他叫我一声爸爸,并且试着接受他,爱护他。”
他还想说:“雪儿,对不起,当年是我伤你太深,是我不懂珍惜,是我混蛋,如今我别无所求,只求你像七年前一样待我,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我……”
这一夜闵关绍想了很多很多,最后吻着女人的唇悄悄的为她系回丝巾,垂眸,看着身下毫无防备的睡颜,执起她的左手细细描摹着那枚寓意“重逢”的婚戒,深眸一片柔软,继而铁臂一伸,揽着她的纤腰沉沉睡去。
女人,只要你肯回到我身边,只要你心里还有我,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计较,什么都不在乎。
后山鸡鸣唱响新的一天,东方,一轮旭日冉冉升起,瞬间洒遍大地。
从寒冬到暖春,从黑夜到白昼。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
顾映雪一觉睡到自然醒,睁眸,眼前沉着一张俊脸正在她嘴巴上啃。
意识恍惚了一阵,蓦地脑海中拂过昨晚的情|事,霎时羞得小脸酡红。
“雪儿,早。”闵关绍含糊的应一声,“既然醒了,那我们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