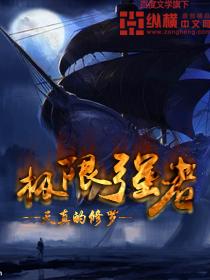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铁血幽灵站队 > 第十二章 主仆分明(第1页)
第十二章 主仆分明(第1页)
领头男人虽然被训得低下了头,但刘国栋的一顿骂,还是让他听到了希望。
他向后招了一下手,十几个人这才背起枪,稀稀拉拉、无精打采地蹭了过来。“我们有十七个人,是从喀布尔来的。其余人都被打……死了,就剩下我们这些人。”
“负伤的、不能带走的,都被你们自己打死了吧?你们这也叫军队?”刘国栋看着衣衫破旧、叫花子一般的队员们,嘴里不屑地叱道,“要带你们走也可以,但要看你们象不象一群男人,敢不敢跟着我们打下对面这个山头哨所?”
“打哨所?你确定?”
哈瓦什显然大惊,“你们不是开玩笑吧?对面哨所在山头上,居高临下,少说有几十人驻守,还有一门大炮。可我们呢,加上你们,我们才十九人。我们子弹每人不超过几发,我妻子希莎尔玛·哈瓦什,还不会打仗。”
“军中无戏言,我跟你开玩笑?不敢打仗,你当什么抵抗组织?那就一边玩儿去,各走各的。本来也不需要你们,我们两人,再加上小地主三个人就能打下来。”刘国栋摸摸小地主的头,不容置疑地说。
小地主也傲慢地掉过头,瞅了他们一眼,又掉过头去,不理会他们了。
那个叫希莎尔玛的女人,却忽然说话了,“你们敢打,我们也就敢。真主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跟你们***。”
“当家的说话,女人别插嘴!”刘国栋故意说道。
“你……”女人掀开围在脸上的厚厚的棉质黑头巾,怒视着刘国栋。刘国栋瞅了她一眼,大大的眼睛圆睁着,棕色的皮肤,年龄也就不到三十岁。从气度就能看出,和哈瓦什等人根本不是一个阶层。
虞松远见状呵呵地笑了起来,他给了一颗烟给哈瓦什,并给他点着,又看看正与刘国栋对峙着的希莎尔玛。
这是一个年轻女人,头上用黑色大头巾,将脑袋全部裹了起来,只露出两只亮晶晶的大眼睛。身上同样披了一床军毯,里面穿着山人伊斯兰共和国女性难民常穿的黑色罩袍,长及脚面,脚上是一双男式军靴。
从她眼里的目光,从她讲话时不容置疑的声音和神态,从哈瓦什和其它队员对她的态度,虞松远一眼就看出,这分明是一主一仆,还什么夫妻?狗日的,骗鬼去吧你。
“你们到底谁当家?”虞松远故意问道。
见对方尴尬一阵,都不愿回答,他便又掉过头去,开始观察哨所,故意不理会他们了。此时,直升机已经起飞,向贾拉拉巴德方向飞去。但十几名士兵,却并未登机一同飞去。很明显,他们留在了哨所。
“反应真快,这是冲着我们来的。”虞松远说。
看这架势,斯贝茨纳兹已经确定,袭击者逃进了这座大山。大规模的搜山即将开始,必须迅速转移。这里离边境一步之遥,有若干条高山中的小路可以穿越国境。而国境那一边,就是抵抗分子或“圣战者”设在清真之国境内的若干基地。
但虞松远不想冒险,斯贝茨纳兹已经被激怒,肯定会在多条小路埋伏。况且,他内心深处,已经决定带这一小队残兵败将一起走出困境。如果不带他们走,凭这一群乌合之众,很快就会被消灭干净。
退路已经截断,只能沿着大山,向东北方向的阿萨达巴德方向的大山内撤退。
“哈瓦什,形势很严峻,叫你的人全都过来。”虞松远说。
希莎尔玛招了一下手,众人都围到虞松远、刘国栋身边。
刘国栋从塑料袋内拿出地图,并指着地图介绍说,“咋天晚上,我们摧毁了贾拉拉巴德机场,炸毁了跑道上的飞机,并袭击了斯贝茨纳兹独立第l54特种兵分队。现在,前面的哨所,他们加强了防守,大规模的搜山很快就要开始。此时穿越国境,相当于去送礼。因此,我们准备顺着大山,向阿萨达巴德方向撤退,伺机进入库纳尔河对面的大山里。你们有什么打算?”
“我们已经被堵在这里一周时间了,吃的也没有了。子弹也很少,我们跟着你们吧,大家一起撤,互相有一个照应。”希莎尔玛看着虞松远说。
“你们到底谁是当家的?”刘国栋又故意戏谑地问道。
希莎尔玛干脆利落地说,“当然是我当家,这还用问。哈瓦什和他们,都是我父亲卫队的士兵,也是我家的仆人。哈瓦什是队长,马哈茂迪是副队长。哈瓦什是为了掩护我,才说我是他妻子的。”
虞松远和刘国栋都笑了,哈瓦什的脏脸肯定也红了,可惜看不出来,但头却低下了,眼睛看着地面。虞松远能清楚地看出哈瓦什低头的意思,这小子占老便宜了,还绝对是当真了的,他心里一定是爱着他的主母希莎尔玛的。
“好好,谁当家都可以。你们跟着我们可以,但我要强调战场纪律。你们都认真地听着,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原来的组织,现在属于‘高原狼抵抗组织’。希莎尔玛跟着我们俩,其余16个人分成两个作战组,要完全服从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军中无戏言,违者军法从事!”虞松远吓唬道。
希莎尔玛果断地说,“没问题,全都好说。哈瓦什带一组,马哈茂迪。哈比卜带一组,我们完全听你们指挥。其实,我们是看着你们从飞机上掉下来的,象两块大石头。你们从河边谷地一过来,我们就一直跟着你们呢,我们相信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