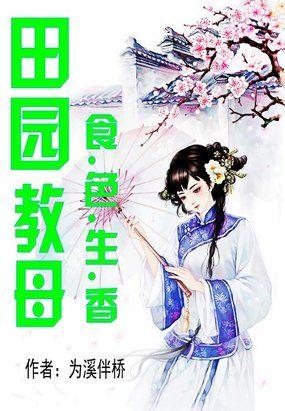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红楼之他不想弯微博 > 第147章 0147(第1页)
第147章 0147(第1页)
晋发。0147借名姓偷得数年存,想原由数遍往昔债
那甄家原也是命运多舛。甄家的老爷甄士隐是远近闻名的慈善人,与他夫人情深意笃,只是命中无子,半生才得了一个姑娘。偏那姑娘才养了没几年,便被拐子拐去了。甄老爷并上他夫人只有这一个女儿,爱得如眼珠子一般。骤然失女,怎能不痛。后甄家的宅子也一把火烧了,甄老爷并上他夫人就此搬走,后又零碎听过一些信儿,近两年竟是半点没有了。
那甄老爷原于石婆有恩,石婆听了,便肃容问道:“果然?”
老李家的被她唬住了,自然什么都说出来,什么都听她的。当下颔首,道:“她说是这样,只是不知道真假。那甄家比上不足,我们看着已是大户人家了。虽我们平日里都听说甄家再没人了,那甄老爷也没兄弟姊妹的,到底有没有,咱们也并不十分清楚。”
正是这时候,外头寒芸道:“妈,我给莲溪换了衣裳了。”说罢,便打帘子进来。
石婆忙叫寒芸搬个小杌子过来,让莲溪坐了。莲溪让了一回,便在杌子上坐下。石婆与老李家的道:“天也不早了,该吃饭了。赶巧寒芸才说想吃馄饨,我就叫小子出门去,割了一方好肉,才剁了肉馅的,老李家的,你倒该留下吃碗馄饨。”
“这怎么好呢,倒来赖你一碗馄饨。”话虽如此,却并不曾推拒。
石婆便与寒芸道:“你去做饭,我和你李婶子再说说话。”
寒芸应了,又出去。
石婆这才看向坐在杌子上的莲溪。原贴在面颊上的碎发已梳顺了,发髻散开落在身后,因着湿透的缘故,并不曾梳起。衣裳已换了,乃是石婆她大女儿原先穿过的就以上,绾色衣裙穿在身上,虽是旧衣裳,却仍显出贞静并上秀气来。
“徐姑娘,方才你李婶子都与我说了。你是好人家的姑娘,又是有亲眷在这里的,犯不着做伺候人的事。照我说,你不如在我这里暂且住下,待寻找甄老爷他们,欠人的钱,不都有了?”
却见莲溪摇头,口中道:“有些话,我也不必瞒着妈妈。甄家倒也算是我外祖家,因甄家老太爷原先住在外头的时候,与我外祖认得。甄老太爷他们家是独传,纵妻妾纳遍,也只得了一个儿子。甄老太爷想着我外祖家有儿有女的,便叫他夫人认了我母亲做干女儿。因我们家出了事,外祖家也不成了,我妈就叫一个奶妈子陪着我往苏州来投奔甄家。只是料不到甄家一把火烧没了,甄老太爷并上甄老太夫人也一早去了。我万般无奈,便四处找人去问。原来我|干舅舅自家里失火,便住到舅妈娘家去了。没两年竟然跟着道士出家去了……虽我妈与他们是干亲,到底现下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了。舅舅又走了,舅妈自个儿还在娘家住着,我这会子又巴巴的投奔了去,算个什么呢?”
莲溪这番话,乃是真真假假掺着说。甄老太爷确然有这么个干女儿,只是干女儿确然也养了一个女儿,确然是姓徐。只是这位徐姑娘命薄,同她一起关在牢里的时候因着一口热水也吃不着,竟然一病死了。她因与这位徐姑娘原先是闺中密友,徐姑娘零零碎碎提过一些。后她逃出来,便顶了徐姑娘的身份。那徐姑娘原闺名唤莲嬉,她便改了末尾一个字,成了徐莲溪。
这七弯八绕的,那些人要找着自个儿,想必要费一番工夫。
石婆听了,一面深敬她年纪小却想得周到,一面叹息:“好丫头,偏是你们家苦命。甄老爷这样的大善人,偏落得那么个下场。那年我们寒芸病了,偏我们当家的也病了,两个人都病着,我竟拿不出钱来给他们治病吃药。还是老李家的你告诉我,甄老爷是乐善好施的人,我便去求了,原只当门也不能进的,没料到甄夫人竟然命她身侧的杏姑娘送了十两银子出来。说是老爷和太太都说了,谁都有难的时候,不必急着还,快请医吃药是正经。因着这个,寒芸才捡回了一条命。只是我们当家的没能留住,一病去了。”
这原是她极伤心的事,现如今提起,口吻平淡,语气也十分平缓了。
老李家的也长长叹息,道:“甄老爷确然是个好人,只是哪里知道是这样的命。他时常抱着他们家那姑娘出来玩的,我远远见过,生得何等出众,只怕和面前这莲溪也差不了多少。只是他娘的那作死的人拐子,拐了旁人的命|根子去糟蹋了。家业烧得精光这也不算什么,但凡那个女儿还在,甄老爷也不至如此了。”
石婆摇了摇头,便与莲溪到:“好孩子,你若要留下,便留下罢。你这样的人品样貌,出去了不至饿死,到底有个正经的活路也难。你在我这里住两年,学些规矩,我好好给你择一户人家,你做几年事,攒些银子,好日子在后头呢。”
当下石婆再不有疑,取了卖|身契来,叫莲溪按了手印,这便成了。莲溪那日卖|身的银子是五两,原要匀出一份来给莲溪口中的掌柜送去。只是那老李家的见财起意,竟将银子昧下了,并不曾送过去。
乃至后来,林家夫人回乡,因宅子里缺人手,便要买两个丫头使唤。石婆便领了人过去,果然林夫人一眼相中了莲溪。林家素来是书香之族,钟鸣鼎食的,石婆因想着那是个好去处,便一心地为莲溪高兴起来。
只是她不知道,莲溪成了珠珰后,倒过了一段好日子,贾敏并上林海待她极好,便是林家的哥儿林玦,也拿她当亲生的姐姐一样。只是终究要来的躲不过,到底还是被他们找着了。他们不仅要她死,还要她死得那样凄惨,声名狼藉!
石婆去后,林玦与慕容以致相对而坐,二人皆是郁郁,久不能言语。
许久,慕容以致唤道:“欣馥!取酒来!”
不多时欣馥便捧了酒进来,林玦将她摆在自个儿面前的酒盅推远,道:我不吃酒。“
慕容以致便自斟一盅,仰头吃尽了。许是吃急了,酒液顺着脸侧滑入衣襟,凉入肺腑。他“嘶”了一声,又自倒了一盅酒,淡声道:“昔日归盈面上瞧着是个极文静的姑娘,实则骨子里很顽劣。她是舒郡王府的大姑娘,父亲是同先太是挚友,母亲是今太皇太后的外甥女。从小到大,她要什么没有,便是太皇太后待她,也格外疼爱。她那时候常来宫里,总偷偷央我教她射箭骑马。我那时候正是最不羁的时候,怎么肯教一个小姑娘这些。故而便常常借口说有事,留她一个人在那里,自出宫去。现下想起,却很后悔。先太子病时,我在边疆打仗。回来才知道,先太子已然被废,后不久便去世了。便是舒郡王府,也一夕之间崩溃离析,原先的太子一脉纷纷落马……我奉太皇太后的命,暗中安顿了表姐,便寻归盈,只是再寻不见。我那时候,实在很意气用事,觉得我哥子,现如今的太上皇,实在心狠手辣,不通人情,便是连亲生的儿子,也能下得去手,一怒之下便请命去了边疆,再不肯见着这个满堂富贵。”
说话间他已接连吃了好几盅酒,林玦见他说罢了,又将一盅酒送至唇边,陡然伸手将他手腕拦住:“你信不信我,这杯下去,你就醉了。”
慕容以致定定瞧着他,也不见动作,只动了动唇:“我酒量极好。”
他将酒盅取下来,目色平寂,口吻极淡:“原与酒量没什么相干,愁肠百结的时候吃酒,最容易醉。醉生梦死,现下还不是时候。”他抬起手来,慢慢将那盅酒倾在地上,“聊以此酒慰长姐,弟立誓,必然为姐姐你洗清这份耻辱冤屈!”
他从未那样恨过一个人,今次才明白,何谓恨不能食人血肉以饱腹。
太上皇纵然疑心先太子,发落了先太子那一脉的人,也不必对舒郡王府里的人这样心狠手辣。到底苏归盈认真算起来,还要喊他一声叔叔。
要杀尽先太子一脉人马,对此报以深恨的,只有那一位……只是这正是林玦想不通之处。那一位对舒郡王深恨倒也情有可原,舒郡王与先太子是挚友,为先太子做事,挡了他的路,想必是寻常。只是他对一个姑娘这样赶尽杀绝,又是为着什么?
林玦眸色暗沉,心中如此,不由问出声来。
慕容以致摇首,道:“那一位的心思诡谲莫测,我猜不着半分。谁挡了他的路,他就要谁死。东太后原先那样待他,他便要东太后的儿子死,抢了她儿子的皇位,将她最看重的名分地位尽数掠走。舒郡王跟着先太子做事,挡了他的路,他便要舒郡王妻离子散,颠沛流离。这都有理,只是归盈……”他言语艰涩,“归盈那样小,绝不会得罪他。”
林玦不由敲打着桌面,眯起眼睛,呢喃道:“为着什么呢?”
欣馥站在一旁,见状上前两步,轻声道:“林大|爷,那位何故如此待苏姑娘,奴婢不明白。只是有桩事,我们爷想必是忘了,我倒还记着……”
“什么事?”
“苏姑娘并上那位,原先东太后在太上皇并上太皇太后面前提过一句,说是苏姑娘的人品样貌都很好,堪为皇子正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