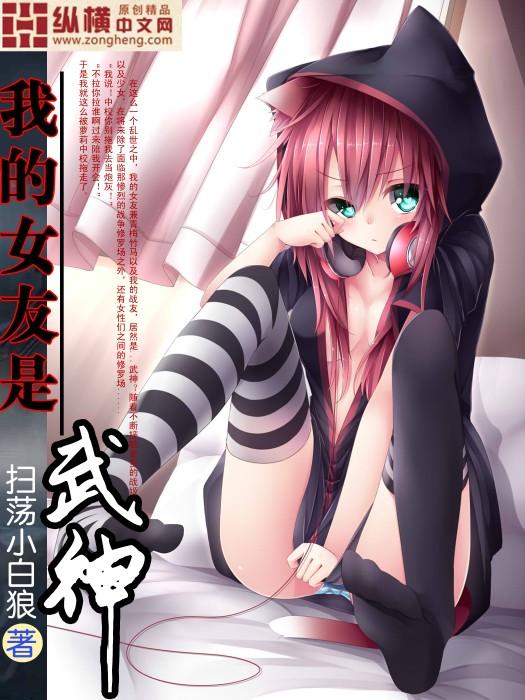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嫁到漠北以后全文阅读 > 第74章 提亲(第2页)
第74章 提亲(第2页)
来人是殷墟。
魏砚搁置下刀,系了外氅革带出了屋。
他这身装扮分明是从榻里刚出来的,不甚雅观。殷墟见他这副模样,又看到他脖颈的抓痕,笑意深了,没说什么。
魏砚关好门带人往旁侧的屋走,“外祖深夜前来是出了事?”
两人落座,魏砚曲起腿,一手搭到膝上。
殷墟道:“如今上京事平定,我打算明日一早就动身回祖家。”
见他正要说话,殷墟摆了下手,“你不必劝我,我一把年纪了,无心朝政,只想回去养老。”
魏砚合起唇,略点下头,双手抱拳,“明日我带人送您一程。”
“不必。”殷墟推拒,“我能出什么事,有来时带的人就够了。”
他看他一眼,忽道:“你若一心回漠北,沈岁寒那一关可是难过。”
魏砚薄唇抿了下,沉默不语。
殷墟从袖中掏出一物置到案上,“我与沈岁寒的父亲有些交情,这是他给我的信物,你去沈府时带上它,沈岁寒不会有意为难你。”
魏砚掀眼,接过翡翠的玉佩,玉佩呈弯月状,是有两块拼凑在一起,这是其中一块。
“多谢祖父。”
“不必谢我,除了这些,我也没别的能帮上你兄弟俩了。”殷墟沉下声,“现在大局已定,你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就别再后悔,能去镇守漠北也好。”
“景儿自小心思就不同寻常,他虽敬你是兄长,但君心难测,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镇守漠北反而也是一道护身之法。”
魏砚咧了下嘴角,满不在乎道:“我此生只想永驻漠北,护住边关。除沈家幺女,再别无所求。”
听他所言,殷墟捋着白须,笑,“任谁能想到生性放荡的淮安王还是一个情种。”
魏砚灌了口酒水,没否认。
“外祖还有一事想问你。”殷墟又道。
“外祖请说。”
殷墟看着他,“殷止可是在漠北?”
魏砚沉默了会儿,点了下头。
“当年究竟是怎么回事,殷止他不是宋倾的军师?那事过后,宋倾为何突然没了音信,再无人提他?”殷墟叹了口气,“当年我本以为是因你母亲亡逝才离得上京,可又觉得其中隐瞒了什么。”
魏砚又灌了一口酒水,脸上堆笑,“正如外祖猜想,当年之事确实因为我母妃的死,我才离开上京,远赴漠北。宋倾战死,军师自愿跟我同去,其他没什么隐瞒的事了。”
殷墟看出他脸上的神情有异,是不想多说了,叹息道:“也罢,你一向有主张,我便不多管了。”
烛影晃动,殷墟站起身。
“我送外祖。”
两人一同出了门,马车远去,魏砚回屋时动作放轻。
她是累极了,枕在里睡得熟。
魏砚坐到榻边,抚着她的发顶。她头发生的好,乌黑亮丽,摸着手感像上好的绸缎。
掌心触到她的脸,肌肤白嫩,生着细小的绒毛,触着他,面如云霞。
他俯下身,吻着她的唇,她眼睫颤了下,水眸掀开,“做什么?”
魏砚没说话,目光不离她的脸,细细地盯着,沈瑜卿回视他。
过了会儿,他手伸进去。
沈瑜卿目光晃了下,他抬她右腿,浑身的肌肉绷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