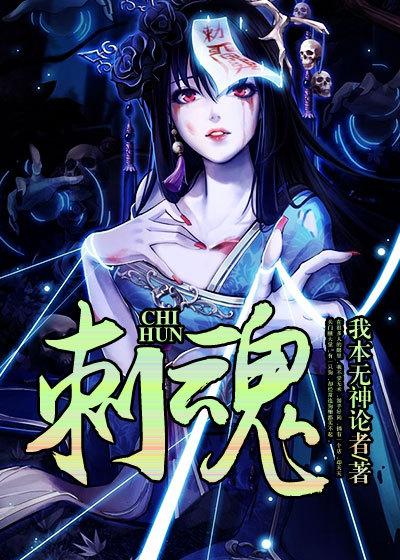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维多利亚女王英剧 > 第30章(第1页)
第30章(第1页)
1851年10月,一位匈牙利革命的领导者科索兹流亡到了英国,对这样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女王政府当然恨之入骨,而帕麦斯顿却表示要在伦敦的家里接待这位匈牙利的爱国志士。他们的矛盾再一次尖锐,帕麦斯顿甚至想以辞职相要挟,最后还是屈服了,但帕麦斯顿的同情革命政治态度却因此而远近闻名。几个星期以后,一个来自芬士伯雷和艾林顿的激进派团体求见帕麦斯顿并呈上一份请愿书,上面将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蔑之为&ldo;丑恶可憎的凶手&rdo;和&ldo;残忍的僭主与暴君&rdo;,作为君主专制下的英国大臣,帕麦斯顿当然在表面上对这些措词表示了反对,但这种反对是温和的,而且在这些温和的谈话中他听任自己真情实感以一种漫不经意的方式流露出来。
帕麦斯顿的言行立即招致了朝廷的愤慨与咒骂。维多利亚夫妇深感手下的这位外交大臣比以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显得危险。
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iddot;拿破仑政变。路易&iddot;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iddot;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三、克里米亚枪声一响,女王夫妇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麦斯顿的垮台,标志着阿尔伯特在维护王权专制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ldo;改革法案&rdo;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ldo;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rdo;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阿尔伯特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后曾与阿尔伯特站在一边的首相约翰迫于议院的压力被迫辞职。由辉格党人和比尔的追随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顿勋爵,而帕麦斯顿再一次进了内阁。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从帕麦斯顿事件中人们感到社会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这个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职责在实际上却由一个在宪法上无明文规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对于君主有着模糊而又无限的影响,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也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融自己个人的存在于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弥补其作为一个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职责时难免会出现的各种缺陷,时刻密切地关注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使她得以在面临各种纷繁而艰巨的问题或职责时能随时给她以忠告和支持。这些问题或职责有时是国际事务方面的,有时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社交方面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作为当然的一家之长,她的家务总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员通信交结中的惟一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师,女王的私人秘书以及她的终身大臣,他有这个义务。
&ldo;这是相当危险的&rdo;,国民却总是这样认为。
于是所有的怨恨一齐发泄在这个异国青年甚至还包括那个受异国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当时正处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帕麦斯顿极力主张向俄宣战而阿尔伯特罢免了他,因此到处都在扬言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俄国的哈巴狗,他将英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英国的敌人的方向。所有的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报刊,公众集会上的反复张扬,私人谈话中的细致渲染,使一切变得更加极端而离奇。甚至在伦敦街头叫卖的半便士一张的小报上也刊登有这样的打油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