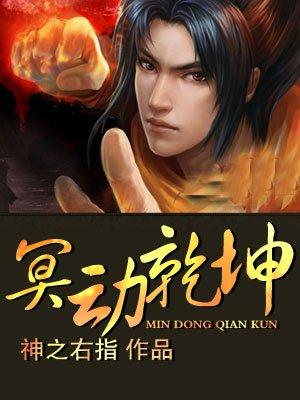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总裁上位史 > VIP183你毁了我(第1页)
VIP183你毁了我(第1页)
送完秦子俊回屋,刚走到客厅,沙发上的包里,手机就响了。睍莼璩伤
一看来电就没有了接听的冲动,但手机铃声却不管不顾,疯狂而执着的响着。
苏炔走过去一把拿起来,冷着脸就吼,“什么事!”
电话那头,一把低沉如这般安冷的夜的男声,低低徐徐,“秦子俊走了?”
苏炔立刻反应过来,“魏立名是你的人?这么说,是你让他子俊半夜出差的?”
那头,低低的笑声似青灰的烟雾,无形中能把人缠死,“这就是权利的好处,我可不想我的女人被别的野男人染指。”
苏炔腮帮子咬的铁紧,“他是我丈夫!你才是那个野男人!”
男人啜一口烟,神色淡淡,“谁是你男人,你问问你下面。”
苏炔脸一下子烧红,气息喘伏,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
“感谢我吧,不然你今晚得遭多大的罪。”
感谢他?
苏炔狂笑不止。
感谢他在她婚后不知死活地从国外归来?还是感谢他万恶不赦地搅浑了她安宁的生活?
她这幅身体,从结婚之日起,就该是秦子俊的!
“寒渊。”只撕心裂肺地这么一声,眼眶就湿透了。
泪珠钻入最颤抖的唇缝间,她尝着那份心酸的咸味,咬牙,不哭出声音。
但寒渊是谁?
不难听出她声音里异常艰涩的哽咽。
修长皙白的指间蓦地顿挫了一下,烟灰掸落一地,似乎是被灰白烟雾熏痛了眼睛,他眯起眸子,神色沉淀下去,“阿炔,对不起。”
她笑。
如果一句对不起能解决,还要警察和道德做什么?
他不是人。
竟然还有脸高高在上给她打电话在她面前炫耀,他用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利暗地里支配秦子俊出差去了。
这意思,难道是要她对他感激涕零?
寒渊,没有人比你更残忍了。
“是你毁了我,寒渊,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你不是我的谁,秦子俊才是我的丈夫!我和他发生关系,理所应当!而你,去死吧!”
伏敛在苍茫夜色下的男人,眉目一凝,精致的轮廓霎时间青沉了起来。
露台的落地窗大开,很有力度的夜风灌进他刚烈的发丛,长及脚踝的宽大浴袍更衬得他长身玉立,仿佛定在栏杆边上的雕塑。
雕塑,没有表情。
他却是淡淡哼了一声,眸色阴陨,“你这话你是对你自个儿说的吧。顶用吗?没人比我更懂你,就是你自己,也一样。我知道,你不情愿秦子俊碰你一下,虽然知道这和我没多大关系,但我宁愿想成是你下意识在为我守身如玉,就像之前我为你做的一样。”
“疯子!”被他说中,苏炔除了愤恨自己,余外就是狠狠咒骂他。
对,她该死的就是无法堕落到那个地步,就是跨不过那条底线,她感激秦子俊,就算那么想要她,他也没对她动粗或者施暴。
这是电话里这个男人到死都比不上的。
寒渊侧了侧身,关了窗户,浴袍大摆很快在沉闷起来的空间里,安静地垂落着,不再动。
薄唇微斜,低低地笑,“你的形容,我都能接受。”
“你最好去死!”苏炔不介意对他说出最恶毒的语言,是他自找的!
那头顿了顿,声息错乱,一会儿,还是笑,只不过,那笑声显然不如之前邪悦了。
“我死了,我和你姐姐的孩子怎么办?你希望你的小侄儿出生就没有父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