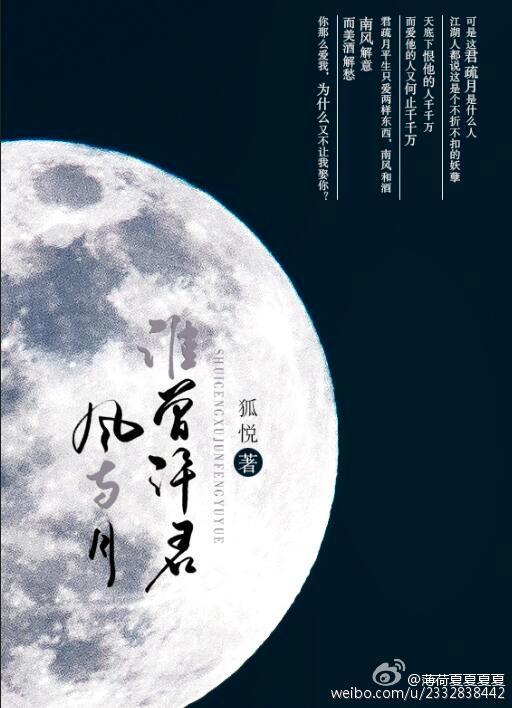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就是妖怪听书 > 第41页(第1页)
第41页(第1页)
另一个哭喊着道:“是呀,我们干什么了?你让我们死个明白啊!”阿破和无双面面相觑,一时语结。是啊,按说这时候这四位的打挨得很冤,他们的坏念头还只是一个设想……阿破迟疑了一下,恼羞成怒,一边继续踩一边道:“就看你不顺眼行不行,妈的老子上辈子杀人都白杀,揍你一顿还需要理由?”这台词听着耳熟——好象是跟《小兵张嘎》里胖翻译官学的,原词是: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白吃,吃你个破瓜还要钱?那是我们四个跳墙看的纳米开光技术在我的面前,摆着一杯刚沏好的,两块五一两的花茶,烟雾袅袅,一张不知道谁丢的上上个月的《参考消息》,我坐在一张带靠背,屁股垫是被一圈图钉按在中央的人造革椅子里,闭目凝思,貌似妖孽……我们的城市已经恢复了平静,或者说,在,一时间社会讨论激烈。我很感谢这些专家,他们简直就是帮我们善后的最强有力后盾。大勇的记忆里,他曾在酒吧和我们相遇并且在第二天来看过小慧,但是他不记得前天晚上他为什么会在酒吧出现,为此他还打电话问过我,我说:“那时你丫喝多了。”这次的倒退,我借助报仇的力量几乎违反了一切制约因素:时间跨度长,涉及人数巨大,而且把阿破和小慧他们都一起带去了过去。后来我有点明白了,那把妖刀能把我带回到6000年前不曾有丝毫毁损,但是回了趟半个月前却被销蚀一光,这说明人类的惯性是巨大的,每抹平一个人的记忆就需要付出无比巨大的力量为代价,我们这次能平安回来实属侥幸!也许我这么做破坏了一些平衡也改变了一些人的命运,或许照着他们原有的轨迹有人可能买才票成了亿万富翁,但我不后悔,我毕竟挽回了不少家庭的幸福,相对个别人的运气,我宁愿选择我们的城市遗忘掉那把刀带来的伤痕。我有时候挺多愁善感的——主要是我觉得我做的是好事,得自我伟大一会。超市里,小绿踮着一只脚站在柜台后面,我很好奇这个姑娘为什么没事就喜欢站着,她手里拿着一支笔,随意地在自己钉的白纸本上划拉着什么,往往眼睛望着一个地方盯老半天也不动一下,与其说她在出神,倒不如说她是在沉思什么,有时候她发现有人在看她,就会微微脸红,然后装出要专心工作的样子,可是没多久就又情不自禁了。王成坐在超市的门口晒太阳,高大全现在已经没时间听他吹牛了,于是他就找了几个孩子当听众,孩子们开始还饶有兴趣,但是听得多了,他们也纯熟了,全部能背诵,再一听就烦厌得头痛。“我真傻,真的。”王成开首说。“是的,你单知道反政府武装在丛林里布满了防步兵压发雷,可没想到树枝上也装了牵绊诡雷。”他们立即打断他,走开去了……高大全是我们最近最对不起的人,那天我们把他扔在黑山口,谁也没想到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如果是我们,可能会想一些权宜之策先回来再说,但是高大全是神族,他的信仰不允许他做出有违道德准则的事情,所以他就一路问当地的野狗一路走了回来——我们再见他是两天以后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吃饭问题的,但是从那以后他对骨头很感兴趣,尤其是那种被人啃过的。为了弥补犯在他身上的过错,我加紧为他在我们街口开了一家宠物医院,因为他没有任何医师资格,所以表面上只能是卖些宠物用得着的东西,比如狗粮猫粮,笼子铃铛什么的,有时候虾仁和野猫别动队的成员会来客串一下模特,它们钻在笼子里或戴上铃铛,让街上路过的那些宠物看自己是多么漂亮。自然,只通过几个例子高大全就已经开始名声雀起,找他看病的宠物多了起来。我曾教唆他,去指使那些宠物隔三差五地装病拖着主人来照顾一下生意,反正那些人大多有的是钱,但人家是神族嘛,还鄙视了我,活该他对骨头感兴趣。这天下了班,我们叫上高大全上家吃饭,仍旧是小慧下厨,无双和阿破在客厅看电视,无双无聊地换着电视频道,中央某台,赵忠祥那神神叨叨的声音响起:“每年一到迁徙的时候,就会数以万计的角马从东非的塞伦盖蒂平原向西奔走……”高大全刚进门在我的提示下边换鞋边说:“快换台吧,看了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