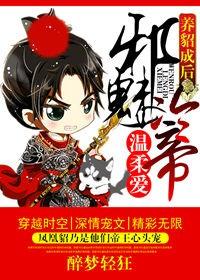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飘渺烽烟漫画免费 > 第522章(第1页)
第522章(第1页)
婷婷答道:“臣妇只是臣妇,不可逾越礼法,更不可调遣国家武将和大王的虎贲卫队。彼时臣妇年少,不知天高地厚,一刻高兴,居然就接受如斯重赏,后来又因忘性太大,浑然忘却此事,今天臣妇收拾行李,见到玉牌,才回忆起往事。臣妇这么多年都占着这逾制越分的权柄,实在不成体统,便是现下奉还,也为时太晚。臣妇无知又大意,恳请大王恕罪!”
嬴稷立刻道:“小仙女多虑也!我授你特权,正是想让你凌驾于礼制律法,我乃大秦之主,既是我亲自授权,便没有‘不成体统’之说,你绝无罪愆!”他拿起玉牌,双手捧给婷婷,柔声道:“请小仙女留着玉牌,我许你的权柄,你继续持有。”
婷婷道:“大王美意,臣妇铭感,但臣妇万万不能再持有这权柄。”
嬴稷胸口一阵酸痛,双手隐隐瑟缩,颤声道:“小仙女,你执意归还权柄,可是为了帮白起避嫌?”
婷婷平素不喜过问政事,但既为重臣之妻、半生陪伴夫君效力于朝廷,就免不了耳濡目染朝中万象,对于那些攘权夺利的明争暗斗,她虽无甚兴趣,却也不是完全懵懂。此次白起遭受贬谪,她自然明了其中有国君疑忌的原故,因而她重见玉牌虽是事出偶然,但上交玉牌、奉还权柄却的的确确有减轻国君忌心的意图。
“大王,臣妇本就不该握有此等权柄。”婷婷语声平和的道,“至于夫君的事,臣妇诚然也企盼能减少您对他的不满。”她措辞谨慎,用了“不满”二字,而非“顾忌”、“猜疑”等折损君主威风的词语。
嬴稷喟叹道:“小仙女,我跟白起抵牾不和,与你并不相干,你不用归还属于你的权柄。”
婷婷摇一摇头,道:“夫妻一体同心,夫君出了事,妻子断不能置身事外。”
嬴稷心中酸楚,眼睛里也有难忍的酸意。他仰面深深呼吸,缓和了许久,方又垂首凝视婷婷,问道:“小仙女,你恨我吗?”
这一问突如其来,婷婷冷不防吃了一惊,抬眸愣怔的看着嬴稷。
嬴稷长眉皱拢,苦笑道:“希儿说,你不恨我,我当时听了很欢喜,可后来再一思量,你怎会不恨我?而我又凭什么奢望你不恨我?”他的表情惨淡无比,但双眼的光亮仍充满温和,脉脉笼罩着婷婷娇小纤弱的身影。
婷婷宁定了心神,又低头伏拜,道:“希姐姐很了解臣妇,臣妇确实不恨大王。虽然夫君受到贬谪,但我们夫妻俩原非贪权之人,所以不会因失权而怀恨。”说至这里,她顿了一顿,唏嘘着续道:“若非要说臣妇存着什么情绪,那便是臣妇担心将士们的安危,以及臣妇即将远行,很舍不得咸阳的亲友们。”
嬴稷双手紧握玉牌,缄默须臾,嗫嚅道:“不只是今回白起的事……这之前还有好几件事……”
婷婷耳闻此言,一颗心沉了下去,乌眸悄然闭合。
嬴稷用力喘一口气,直说道:“当年尔祺、尔瑞惨死,主谋是我。四贵失势,冉舅父迁居陶郡,母亲晚年不豫,亦是由我所致。长平之战,赵军易帅,虽说是赵王自有主意,但我也确实设计加以煽动。这些事,这些我多年掩藏的机密,小仙女你早就知晓了吧?”
婷婷追思着尔祺、尔瑞、魏冉、太后、赵括等人,哀恸难抑,不由得泪如泉涌。
她生怕大哭失仪,遂稍稍抬身,伸袖擦拭泪水。
嬴稷眼见婷婷落泪,心里霎时涌出无尽的怜爱、无尽的歉疚,不禁张开双臂要去拥抱她。但动作做了一半,他陡然警醒:“小仙女端雅高洁,且是我的恩人,我怎可无礼冒犯她!”即缩回手臂,不敢轻举妄动,强自苦受满心焦灼。
只听婷婷小声道:“大王所述之事,臣妇是前年听闻的。”
嬴稷颓唐的点了点头,道:“恩,这些事桩桩属实,并非有人捏造。”
婷婷默然,眼角又滑落一颗泪珠,晶莹剔透,慢慢掠过雪白的腮颊。
嬴稷心似刀割,惨恻道:“小仙女莫哭,你只管骂我、报复我,我甘愿承受,绝不怪你。”
婷婷眼中泪水流转,幽幽的道:“大王切勿多心,臣妇从没恨过您。”
嬴稷双目直勾勾盯着婷婷,神情既惊异、又困惑,道:“小仙女,我迫害了你的多位亲友,现今又整治你的丈夫,你……你当真不恨我?”
婷婷道:“亲友遇害,臣妇痛悼,夫君受挫,臣妇怜惜,臣妇的情愫便是如此,臣妇对大王绝无恨意。”
嬴稷眼睛红热,问道:“你为何不恨我?”
婷婷答道:“灭义渠、削四贵、长平之战、邯郸之战,均是国家大事,大王乃一国之君,为国家大事筹谋部署,天经地义,纵使目的与结果不合臣妇心意,臣妇也不可因私心而怨恨大王。”
嬴稷愕然,旋即一声慨叹:“是了,小仙女一向恪守君臣之道,是忠君的贤臣。”嘴角微微含笑,脸色却依旧忧郁,更夹杂莫可名状的失落。
“小仙女,我从来没想用君臣之道约束你,”嬴稷苦涩的道,“所以你也不必为了遵守君臣之道,压抑了你的恨意。”
婷婷摇头:“大王,就算不依君臣之道,臣妇也不恨您。”
嬴稷身躯一震,惊呼道:“小仙女,你说的是真的吗!”
婷婷缓缓抬起脸,一双亮晶晶、泪盈盈的灵动乌眸和婉的望着嬴稷,道:“依君臣之道,大王是臣妇的君上,不依君臣之道,大王是臣妇的亲友。臣妇不恨君上,更不会恨自己的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