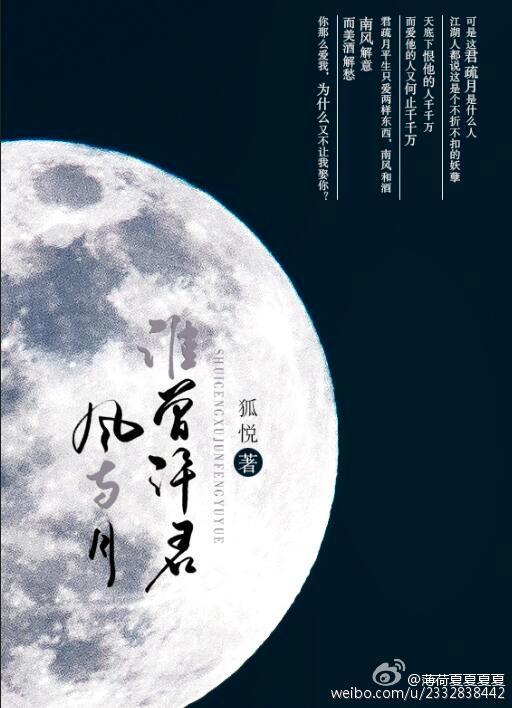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唐门密室 微笑的猫 > 第69页(第1页)
第69页(第1页)
唐缈试图停下,并扭头观察情况,但被淳于扬揽住腰往前猛带,对方力道如此之大,令他几乎绊倒。他喊:“哎哎哎哎哎!!”淳于扬从嘴里摘下手电筒塞给他,自己则紧紧抿着嘴、憋着气,面色铁青,一副快死了的模样。唐画小棉袄似的帮他捂住鼻子,可惜无论怎么捂,臭气还是无孔不入。在恶臭的逼迫下,六个人别无选择地跑到甬道尽头,紧贴着冰凉的石壁惊恐不已,此时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知道大事不妙,但又无从应对。离离捂着鼻子喊道:“绳梯!绳梯!”大概她还想着通过绳梯回到地面上去,虽然在那里也被圈禁,但至少还能呼吸新鲜空气。淳于扬居然真就冲向了附近的绳梯,慌手慌脚地在绳结上瞎摸。这人有洁癖,此时最不冷静,因为臭味很容易就把他的理智挤跑了!唐缈扯他回来,怒道:“干什么呢你?把口罩戴上!”淳于扬刚刚摸出口罩,在手电光有限的照明范围内,臭气的源头就出现了——虫。但又跟姥姥养的那些稻虫、甲虫、还有那个神秘兮兮的荧光门卫不太一样,它们移动很慢,数量很多,集体行动。当它们像某种巨型软体动物似的一涌一涌,一蠕一蠕地转过拐角,一点一点地接近后,众人才看出它们是种两寸来长、体态柔软、喜欢抱团的白虫子。换言之,大蛆。“呕……”唐缈吐出了最后一点黄绿的胆汁。淳于扬已经崩溃了,他背靠石壁,瞪圆眼睛,俊秀的鼻梁上一滴滴渗着冷汗,突然抓住唐缈的手说:“把我的颈动脉割断!”“什么?!”“给你刀!快割!”“啊?!”“快啊!”淳于扬暴怒,“别让那些东西在我活着的时候碰我!”他虽年轻,却经历过一些险境,也考虑过自己将怎样死亡。但无论如何,他都不会设想自己被臭气熏天的蛆虫淹死!与其这样,他宁愿自己从未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过!唐缈怎么可能对他下手,再说落榜生连颈动脉在哪儿都不清楚!“淳于扬!你他妈别拽我啊!你他妈清醒一点!”“快割!死在你手上,我至少心甘情愿!”唐缈回手给他一个大嘴巴子:“但老子不当杀人犯!!!”唐缈倒是很清醒,蛆虫带来的气味强迫他极痛苦地清醒,那味儿实在太臭太刺鼻太要命了!学术上来讲叫做“超高浓度吲哚”,足以熏喉咙,辣眼睛,让人高度紧张,深恨五官灵敏,以及欲死不能!周纳德浑身发抖,离离又哭又叫,司徒湖山仰天怒吼:“怕什么也不能怕蛆啊!赶紧拿扁担、拿铁锨、拿铲子、拿榔头来,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这货也奇葩,居然能嚷嚷出一堆手头没有的工具,说他因强烈刺激而突发精神分裂都算是客气的。离离于是骂道:“老畜生,别添乱!”倒是周纳德给了个切合实际的建议:“应该用火烧,快把那两堆绳子点燃,或许能够抵挡一阵!”唐缈一听,赶紧划亮火柴,咬咬牙,鼓足勇气冲了上去。蛆虫潮涌的速度不快,所以距离他们还有三四十米,唐缈撒腿狂奔到接近虫子的那堆绳梯前,与之狭路相逢,感觉这辈子也不可能看到比这更恶心的情形了。无数的肥白虫子在地下蠕动着、翻滚着,铺成毯、抱成团、聚成堆、堆成塔,像夏天粪坑里耸动的蛆,像浓稠肮脏白里泛着绿的恶浪,沿着狭窄的石壁慢慢地、呈圈状地、无法阻拦地朝他逼近。都说蠕虫没有器官,不会出声,其实会的,它们的存在、聚集、移动便是声音。如果要形容得不那么恶心,你们可以想象在黑夜茫茫的天地间,那草木被害虫摧残吞噬的声音;在狂风飒飒的群山林海中,火焰肆意焚烧的声音;以及动物或人在寂静中垂死的声音。唐缈哆嗦着想要点燃绳梯,然而那东西长久存放在地下比较潮湿,火焰一沾上去便灭了,连续划了三根火柴都没点着。在他身后,手电筒已经改由司徒湖山举着,电光因为人的紧张而晃成了一团虚晕。第四根火柴的火焰是被蛆虫潮涌带来的恶臭空气冲灭的。唐缈连忙背过身,用身体护住火柴,用颤抖的手继续划。他咬紧嘴唇努力地维持镇静,脑门上有大颗大颗的冷汗落下。虫潮离他很近,火却始终没能燃起。淳于扬绝望地喊他快回来,他不肯,继续划那最后一根火柴,仿佛和这件事儿杠上了,以至于都没看见那根火柴头上根本就没有火药,就是一根光杆。淳于扬发出了野兽般的哀嚎:“你回来啊——!!!”淳于扬现在最想要什么?想要一把枪,一枪把唐缈毙了;然后想要一颗炸弹,将自己和唐缈一同炸成无知觉、无意识、无边无野的血肉碎片,两人飞上洞顶,落下地面,混作一团,就这么结束吧!!!唐缈终于决定放弃,然而已经太晚。在距离他仅有几米远的时候,虫潮似乎得到了某种冲锋的指令,陡然增高二三尺,夹杂着汹汹的怒气碾轮一般滚过来,几乎刹那间就将绳梯堆以及站在上边的他包围!“……!!”淳于扬一把将唐画揽在胸前闭上了眼睛,司徒湖山和周纳德也闭上了眼睛,连一向冷血的离离都发出了歇斯底里的惊恐尖叫。然而事情发生了奇异的转折——就在几乎接触到唐缈的一瞬,虫潮停了。唐缈维持着阻挡的姿势半蹲着,虽然双目紧闭筛糠一样抖,却像一把剑或者更光明的什么东西似的,将蛆虫集团切开了一个缺口。虫潮停滞,声息未绝,它们翻滚、挤压、叠加、掉落、聚拢、蠢蠢欲动,可仿佛遇到了无形的屏障,再也无法前进。等到唐缈察觉没有后续,偷偷睁开眼睛,它们便“呼”地往后退了一截。唐缈浑身上下一通乱摸后发现没少零件,尝试性地站直了身体,虫子的触手离开了绳梯堆。唐缈被熏得弯腰呕吐,它们又退一截。唐缈再度站直,与其对峙,虫潮距离他已经两米开外了。“……”唐缈突然叫了一声,跳下绳梯堆,蛆虫们便“哗啦”摊开。“……”唐缈猛然捂住鼻子朝着蛆虫们冲去,虫潮立即向两侧分散,给他闪开一条道。“……”好吧,那继续!唐缈做了一个站立起跑姿势,然后大步向被黏液腐蚀过的石径上跑去,隔着鞋底都感到脚下的灼热和腐臭。他的脚底还有伤呢,天啊!!!他好两次失去平衡几乎滑倒,姿势狼狈不堪,但虫潮“忽忽”地急速退却,速度至少是它们席卷而来时的三倍。它们就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拂掸、撕裂、扯烂、碾碎,溃不成军。是唐缈在驱赶它们,就好像驱逐一群羊,驱散一群鸡。唐缈已然理智断线,一边吱哇乱叫,一边将虫子撵过了拐角,撵回漆黑幽密的甬道深处。直到他被脚下一个凸起的石块绊倒,结结实实摔在地上,这才倾斜着身体大吐特吐起来。胆汁和胃液划过食管时又苦又酸,他的喉咙在灼烧,大脑就像挨过锤击似的嗡嗡作响,连带着双耳轰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才听见淳于扬在耳边喊他。“唐缈!唐缈!”淳于扬蹲在他身前,一手捂着口罩,一手拍打他的面颊,不停地重复他的名字,“喂!唐缈!唐缈!唐缈!……”唐缈侧躺在地面上:“……”淳于扬想扶他,但又碍于遍布他全身的腐臭粘液。唐缈有些傻乎乎的:“刚才……出……出什么事了?”淳于扬说:“这该我问你啊!”唐缈说:“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