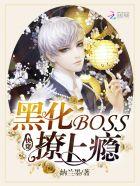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玉露破金风内容 > 第107章(第1页)
第107章(第1页)
查良见状暂且收起了脾气:“老子就当你现在太着急你的杜小姐,所以一时脑子不清醒。与其怀疑我帮杜老爷,不如怀疑我们是不是被骗了。我刚刚想了一下,杜老爷千里迢迢从上海请来的人,怎么这么容易被我们察觉,那还请什么?也许就是故意表面上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反正老子先去给我儿子的法事善后,你还需要什么人,自己让葆生支会我的副官。有新的消息我会再通知你。”
葆生立刻帮蒋江樵处理伤口,忍不住问:“我觉得督军的分析很有道理。先生,你真的怀疑督军?可督军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他有些事还要仰仗先生吧?岂不破坏和先生你的关系?”
蒋江樵没直接回答他,转而提起一件事:“你以为之前他在我婚礼当天把大壮放出来,仅仅发泄苏四小姐小产的怒气?”
葆生还真被他问住了:“难道还有其他原因?请先生明示。”
“你不是说了?他有些事还要仰仗我?”蒋江樵的视线从窗外移进来,“但我结婚前一天晚上明确地告诉过他,我想以普通教书匠的身份继续留在杜府。”
葆生终于被点通:“先生的意思是,督军觉得杜小姐妨碍了你和他之间的共赢关系?”
蒋江樵没再回答,若有所思盯着地面上的地道洞口,顷刻他亲自走上前,阴暗的眸底划过一抹刀锋:“你到下面看看,确认一下有没有荣帮的人留下的痕迹。”
葆生一下心惊。如果是荣帮来的人,那能得手,确实就不奇怪了。他记起曾经出现在杜府外面偷偷跟踪过蒋江樵和杜允慈的两个人,迄今没查到来头,彼时他便怀疑是上海来的人,但阿根否决了他。
而如果真是荣帮的人帮助了杜允慈的逃走,就需要搞清楚,杜家恰好请来的就是荣帮的人,还是荣帮的人专门冲蒋江樵来的。
葆生揣着疑虑遵照指示下去地道,结果没有发现什么,反倒是阿根后来带回消息。
—
杜允慈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也不知道自己昏昏沉沉地睡了几天,只是在稍微有点意识的间隙,记起她跟着舅舅请来救她的人沿着地道的另一头出口处爬出去的时候,被打晕了。而最近几天也一直在被灌迷药。
不是舅舅的人吧?舅舅的人怎的可能如此对她?不是要送她去巴黎的吗?她一定是被人拐卖了……为什么会这样……是谁?究竟是谁?
——杜允慈猛然睁眼。
正坐在床边的人收回帮她掐人中的手。
杜允慈惊惧地下意识往后躲:“你是谁?”
男子样貌秀气,体型纤细,成套的白色西装偏大一号套在他身上,他的短发油光亮丽地四六分,单只耳朵扎了个十分摩登的耳钉,嘴巴上面的两撇八字胡则显露出与他清秀的面庞不相匹配的成熟,至少杜允慈感觉他的年纪应该不太大。
他打量着她,笑了笑,手指伸来她的下巴,颇为轻挑地勾了勾:“你昏睡的时候我还只觉得你是个普通的美人,现在你一动起来我可以理解二哥怎么就被你迷得神魂颠倒藏在霖州不走了。”
二哥?杜允慈颦眉,瑟缩身体躲开他的触碰,结合他的话能猜测的人只有:“你说蒋江樵吗?”
男子饶有兴味:“你不是已经和他结婚了?他还是只告诉你他叫‘蒋江樵’吗?”
杜允慈试探性地使用蒋江樵总提的那个名字:“蒋望卿?”
男子的桃花眼弯起来:“他都能告诉你‘望卿’,没再告诉你其他?”
他的嗓音给她一种掐起喉咙讲话的怪异感,也不知是不是他的声带坏了。不过终归杜允慈并没兴趣探究,正色拿过问话的主动权:“你们和他有仇?”
男子好奇:“你没听见我喊他‘二哥’吗?怎么觉得我是和他有仇?”
杜允慈只能抱希望他是个讲道理的人:“不管是不是有仇,请放我离开。我一定会重谢。你们既然是从地道把我骗走的,应该知道我和他并不是一伙的。”
“‘骗’字可不好听。”男子的手又伸来摸了一把她的下巴,“我们确实是你舅舅请去搭救你的人。”
杜允慈眼底重燃希望。
然而只听他下一句说:“不过你舅舅并不知道我另外有我的目的。你的家人现在都以为你已经乘上开去伦敦的游轮了。谢谢你舅舅提供了机会给我,否则我现在还发愁该怎么把你搞到手。”
杜允慈的脸又急速地一白。
男子登时有些疼惜:“美人,我讲的话很可怕吗?你怎么吓成这样?”
杜允慈的双手紧紧抱住自己,竭力抑制颤抖:“冤有头债有主,你们和蒋江樵无论是什么仇怨和过节,能不能去找他本人?你们既然是受到了我舅舅的委托,应该很清楚我的处境。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和你们一样,和他是对立的关系。我并不是他的妻子,我只是个无辜的人。”
男子笑呵呵:“美人你误会了,我这就是在帮你离开我二哥身边。只不过我帮忙的条件不是你舅舅和你爸爸给的酬谢,而是交换帮忙。我需要你帮的忙很简单,不是要你的命,就是请你在我这里做客一段时间。所以我暂时不能按你舅舅的要求送你去巴黎。”
可这不就是从财狼身边落到虎豹手里,她还是没有人身自由。如果说先前她更多的是因为噩梦里蒋江樵的行为而惧怕蒋江樵、因为蒋江樵的骗婚而抵触蒋江樵,那么现在杜允慈第一次生出对蒋江樵的恨意。他彻彻底底毁掉了她原本安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