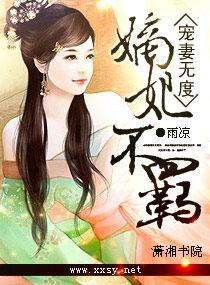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一枕槐安讲的什么 > 第122章(第1页)
第122章(第1页)
她一时没了言语,垂下眼眸小声说:“晓得了。”
沈筵不动声色地弯了下嘴角,在她所有千柔百媚的模样里,他偏生就最爱一个温驯听话。
“吃晚饭了吗?”他问。
“早吃过了。”
苏阑站起身,她缓步踱到客厅的落地窗边,这五六年间,北京的变化很大,从此地望去,入眼尽是云水激荡的拔地繁华。
只是,这窗外的风光不属于她,而窗里的这个人,她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不能消受得起?
她突然问,“怎么又不住酒店了?”
没等沈筵应她门铃就响了。
正好省了告诉她,是因为任命就快要下来,这个节骨眼上,总在酒店住着也不像话,他不想节外生枝。
说穿了,多年修得稳重自持,不等到事情有了十成眉目,沈筵也不肯声张的。
半岛酒店的服务生推了餐车进来,周到的将菜肴摆放在桌上,一壶刚烫好的花雕酒还冒着热气。
他邀她入座,“再陪我吃点?”
苏阑轻曼地卷袖子,给他倒上小半杯酒,“你总这么晚吃饭吗?”
沈筵笑说:“快到年关了,事情多,忙迟了点儿。”
她坐下规劝道:“那也得吃饭啊。”
“你要真放心不下,”沈筵蓦地握住她的手,“就搬出来同我住。”
苏阑急忙把手抽出来,隔了幢幢灯影看着他,“你用什么立场说这话?”
沈筵皱了皱眉,“那你又为什么来这儿?”
苏阑答得很干脆,“来谢沈董抚绥万方的仁德,再就是想告诉你,以后真不必再插手我的事,我们又没有关系。”
沈筵掀起眼皮瞧她,知道她如今长大了想法也多起来,只没想到会这么难,又弄不明白她到底在顾虑些什么。
亏得他还以为,只要他肯结这个婚她就能点头,但他好像忘了,苏阑从不是会在原地等他的人。
前天李之舟那句诛心之论说得很是,没准在苏阑的心里,他沈筵高门望族的,还未必及得上小户人家的平实稳当。
道阻且长啊这路。
“好,”他点头,“我有数了。”
苏阑起身告辞,“那我就先走了。”
沈筵淡道:“我才喝了酒,不便开车,让司机送你。”
按着沈筵一贯的好性子来讲,这已经称得上是不欢而散了。
春节前的一个周末,林静训约了苏阑去长白山滑雪,她难得有兴致,地方又不算远,苏阑当即就在电话里应承下来。
后来想起来,那应该是林静训失常前,上天施舍的,她们最后一点温情时光。
苏阑订了柏悦的套房,就在度假区,滑雪和泡温泉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