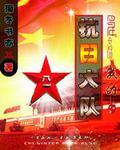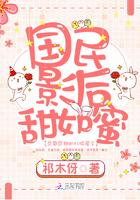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林冲扈三娘大战几十回合 > 第399章(第1页)
第399章(第1页)
不过,高强只说了理想纸币制度的好处,并没有涉及维持这一制度的种种限制,而要维护一个良好地纸币信用,使钱引避免落得象解放前国民党的金圆券那样恶性膨胀,最后导致国民经济崩溃,这中间朝廷的作为起到关键性作用。
好在关于钱引发行的问题,蔡京在与高强交流之后,已经与众手下进行了沟通,今天在殿上提出来,背后有着充分的筹划,因此自然有人将话题引到这个方面。
过不片刻,那林摅又道:&ldo;今我大宋铸钱,每铸十钱须费十三钱,倘若真能如高应奉所说,令钱引可代替货币,则仅此一项,每年便省却二百万贯,诚美事也!况且一旦边中有事,我大宋随时可变纸为钱,亿万军资一朝可具,岂非更妙?&rdo;
&ldo;非也非也!&rdo;高强这时也了解了蔡京的用意,这样危3u&oga;&oga;险的问题,一定要在最开始打好预防针:&ldo;钱引之可行,其本身便是铜钱,只是指代铜钱,非其本身为钱也!朝廷既然无法随手而出亿万铜钱,便也不能出亿万钱引,否则发行出去后,一旦地方没有这许多现钱来兑换钱引,这钱引便又不值钱了,从前交子之贬值,可为前车之鉴也!&rdo;
&ldo;如此说来,到底一届发行多少钱引,才是限度?&rdo;问这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当今最高的决策人,皇帝赵佶。
&ldo;官家圣明,钱引之妙,正在此处!&rdo;见天子关心,高强不敢怠慢,先一个马屁上去,才道:&ldo;今交子大坏,而钱引新发,若能谨慎从事,一除交子陈弊,则为大佳。因此下臣以为,第一,这钱引不可有期限,当言明随时可兑铜钱,地方若发多少钱引,便须得准备好同量的铜钱为本,以备收付,待百姓习用钱引之后,这储备为本钱的铜钱才好渐渐收回。因此钱引之发,当视各路所备铜钱而定。&rdo;
一直没捞到机会说话的张康国,这时候总算抓住机会,冷笑道:&ldo;高应奉,本朝各路铜钱多寡不一,凡多用交子处,都是缺钱的,你反要铜钱多处才发钱引,然则要这钱引何用?见今西北用兵,铜钱运输不易,这钱引多是要用在西北的,照你这般做法,西北的军费要如何去筹集?&rdo;
第四章(上)
虽然站在政见不同的立场,张康国与蔡京党之间争斗激烈,但高强面子上依然恭恭敬敬,先深施一礼,再从容道:&ldo;张相公所言甚是,然下官有一事不明,钱引之发行,在乎西北兵事乎?抑或在乎天下财赋乎?&rdo;
张康国脑子不笨,立刻就发现高强给自己下了个套,这个问题可谓是两面刀锋,答哪个都不大对头的,于是哼了一哼,一脚把皮球踢回去:&ldo;高应奉以为呢?&rdo;
&ldo;呸,你踢皮球的本事再高,能高过我老爹高俅?&rdo;高强给自己壮了壮胆,大殿上侃侃而谈道:&ldo;钱之为钱,天下不当有异,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亦当皆用我大宋之钱,方是理财正道,这钱引若行,仍旧是大宋制钱,不过是换了种表征而已,此乃万世之基,正该缜密筹划,不可急于一时。至于西北兵事所需,我大宋地广粮多,西北童节帅麾下三军用命,胜败岂在乎数百万贯钱引乎?&rdo;
这话其实有些强词夺理,新的钱引发行,正是因为财政上捉襟见肘,而最大的用钱处,非西北莫属。然而高强的优势,却在于童贯现在站在他这边,还没等张康国想好如何反驳,童贯已经跳出来道:&ldo;启奏陛下,高应奉所言极是,钱引之行功在社稷,远惠子孙,不当受制于西北一时之用兵,而坏万世基业。臣不才,愿献一策,可保西北军资丰足,不用国家一文,俾公相可以放手发行钱引。徐徐梳理我大宋币制。&rdo;大宋官场中,称宰相为相公。而蔡京今年年初进位太师,相公一词不足以形其尊荣,朝野都称为公相了。
赵佶听了这会,已然明白了一些,大宋历来财政紧张,许多理财措施都是因应临时的状况而设,结果近似于饮鸩止渴,渐成积重难返之势。现在童贯有办法西北军资不用国家财赋,倒叫他听的新鲜,精神为之大振:&ldo;童卿家。速速奏来。&rdo;
&ldo;陛下,我大宋西北军粮,多与塞下和买,庶民黔首将粮草贩运至塞下,国家再行购进,其间便有许多奸商趁时哄抬物价。比如夏秋收获时,便合力压价收购,后再高价卖于国家,从中牟利,是以西北历年粮草难积,军资之半皆用于此。&rdo;
&ldo;下臣思量来。若这军粮能悉数交于大商家,国家定个大致的数目,令商家自筹自运,塞下只管收付钱粮。则国家亦必俭省多多,更有甚者,可与商家商借数目。待用兵获利之后,令其再取其利。其间无需国家财赋进出,更加轻省了。&rdo;
此言一出,大殿上又是嗡的一声,比刚才更加吵闹,新担任同知枢密院事不久地郑居中笑道:&ldo;童节帅所言倒也新奇,但不知怎么个借贷法呢?又用什么用兵之利让商家取利,难不成我大宋天兵所到之处,要进行掳掠以充军资不成?&rdo;
童贯摇头道:&ldo;郑枢密,何必出此?便以西北为例,我大宋开边之后,西域宝货得以经陆路而行至中原,举凡香料玳瑁良马黄金等等都可在边市上交易,今已开市数次,每次可收数万贯,倘西北平定,西域畅通,想必边贸之盛不下与辽边五市【炫|书|网】。设使我与彼豪商约定,由其提供军粮物资,许以边市数年专营之惠,则国家得军资之饶,而彼商贾得边市之利,岂非两利?彼商人出身,经营边市比我朝廷更精锱铢,想见边市当日益兴旺,日后期限一到,国家或可收回,或预收税赋,继续任其自营,乃至更招豪商,承包税赋,价优者营,岂非皆在国家?&rdo;这个承包的概念,乃是回京途中高强灌输给他的,关于西北军粮的供应,高强已经想的越来越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