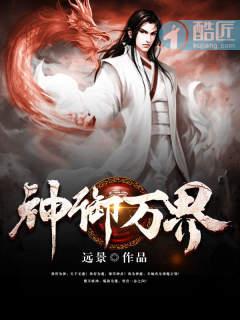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林冲扈三娘大战几十回合 > 第1125章(第1页)
第1125章(第1页)
余睹见高强如此说,亦是为难,想想天祚地脾气,说出这样的话来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此事虽难,总好过任凭局势恶化下去,大宋只有和女真联手,打得辽国万劫不复为止,他这个亡国之臣置于何地?思虑再三,总算被他想出一个补救的办法:&ldo;相公不妨先遣还燕京一役所俘契丹宗室,如萧德妃、大石林牙等人,并送与大辽钱粮若干,稍以为偿,则足见诚意,万事亦可徐徐商议。&rdo;
高强想想也只有如此了,不过这批俘虏虽然是他抓地,他可没权力擅自放了,总得经过朝廷允可,送粮亦最好是经由三省共议,否则要是落个资敌的罪名,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当下便即写了札子,命人以金字牌六百里加急送往京中,随即下令各军与各有司皆安本位,加快燕地部署,大概此札子一上,他自己不久也要进京去了。
到得三月中,种师道率军回转宛平城驻扎,从河间府到此间的各条通道亦已建立,以张叔夜为安抚使的燕山路安抚使司开始运作,朝廷并采纳高强地奏议,以刘彦宗为知燕山府事,左企弓则招入朝中为官,其余燕京降人大小授官有差,多半都是在燕山路安抚使司干事,亦有调入内地为官者。常胜军亦开始分拆,有愿留下戍守燕地的予以甄别,补充进燕人兵员之后加以整训,用为戍边之军,余众则陆续踏上归程,将要回返大名府大营去‐‐这并不全是因为顾念常胜军的主要兵员家乡在此,而是出自大宋&ldo;守内虚外,强干弱枝&rdo;的一贯战略。
诸事粗定,渐渐上了轨道,高强便即率领本部牙兵,带着一众高级俘虏,并耶律余睹、萧特末两个羁留之人,大张旗鼓地回程汴京去了,同行者尚有被招入京城叙官的左企弓、李处温等燕京降人,此外箱笼车辆亦有不少,乃是此役的战利品和燕京土产若干。
途中经过河间府,但见已有铁轨马车川流不息地北上,车上载着大半都是粮食,另有铜钱绢帛等,料
了活跃燕地的经济,便于此地尽快与大宋各地接轨。旅,有许贯忠在汴京调度博览会地资源,高强自是放心,也不大去理。不过这一套对于左企弓等降人来说却是新鲜之极,他们虽然是世代书香,终究局处燕地。又在契丹治下,其国中许多地区甚至还处于易货交易的阶段,对于商品流通地认识尚且比不上南方的士大夫,更遑论和高强这样的超时代理念相比了。
这一路行来,但凡见到些不明事物,譬如钱引,譬如应奉,譬如钱庄等等。左企弓等人照例都要问一问高强。而高强有意炫耀。亦不厌其烦地一一作答,而后在众人惊讶兼赞叹的目光和话语中飘飘然好{炫≈书≈网}久,乃是旅途之中乐事之一。不过,最大的乐事还不在于此,而在一路上官民对于平燕功臣的吹捧和赞颂,这种全民马屁的阵势,可不是等闲人能享受的!
于是且行且乐。高强只觉得身在云端,深深体会到古人所说&ldo;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rdo;地寓意。只是到得大名府,此间乃是常胜军久驻之地,留在当地地军属数万人遮道迎迓,各个喊着自家行人地名字,感谢高强出兵顺利,神速平定燕京。并不为别的。只为这么一来士卒死伤便少,后方少担些心事。
这些人都是军属,当地官吏衙役也不好驱逐。外加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等到艰难行至翠云楼下时,道路已经被挤的水泄不通,也不知谁叫喊一声,都要高相公出来说话,当真是一呼百应,到后来尽是一片呼喊高强的声音。
眼见众情难却,高强只得由众人簇拥着上了翠云楼,站在三楼飞檐下向大众挥手致意,只这么一挥手间,大众已是山呼海啸地叫好,几万人仰着脖子往上看,那场面何其壮观?
这些人当中军属占了多数,其拥戴之心出自赤诚,高强身在三楼高处,却也看得分明,一时颇有些感动,正要说几句话时,身后忽然有人悠悠道:&ldo;衙内,可知功高不赏,情深不寿?&rdo;高强闻言,大喜回头,叫道:&ldo;贯忠,你怎的在此?&rdo;
人丛一分,只见多时不见的许贯忠从翠云楼后进走了出来,依旧是一袭青衫,虽然如今他手中握着半个中国地商事大权,浑身上下却不闻一丝铜臭之气。众人亦多有识得许贯忠的,纷纷以礼厮见。
许贯忠来到高强身边,淡淡笑道:&ldo;小人本在京中预备迎候衙内回京,只是近来耳中颇有些事情烦心,又听闻衙内一路缓行,小人等候不及,只得出来此间,道左相迎。岂料今日万众相拥,道路不行,差幸衙内上了翠云楼,否则小人竟不得与衙内相见矣!&rdo;
&ldo;京中有事?&rdo;再联想到适才许贯忠出场所说的那两句话,高强大脑中已经接近沸腾的血液迅速冷却下来:难道说,已经有人造我的谣言了?
二人相交日久,许多事亦不须明言,只这么眼神无声的交流之间,彼此皆已深知心事。高强向许贯忠微微点了点头,便即回身,向楼下双臂一振,示意大众稍息,那声浪方才渐渐平息。他提起丹田之气,一字一句都传出老远:&ldo;大宋子民听真!此番收复燕云,全赖祖宗威灵,朝廷运筹帷幄,州县馈饷转输,将士阵前血战,方有此大胜,本相不过躬逢其盛,何功之有?&rdo;说罢,亦不待楼下众人回应,当即向西南方汴京所向,双膝跪倒,高呼万岁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