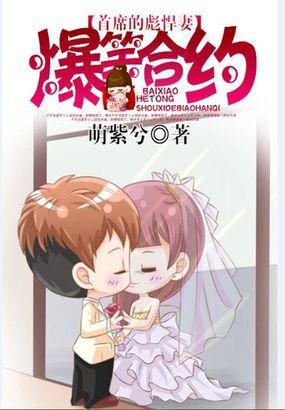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民国女宗师最新章节 > 第177章(第1页)
第177章(第1页)
江水眠捏着那把冰凉的□□,正往夏恒的方向看去,听见这句话,忽然手一僵,头皮一麻。
夏恒笑:“您这话说的我不爱听。我是打算在跟您商量好之前,不动他一下的。可我叫人去他家带他出来的时候还算老实,毕竟几杆枪对准着他。可到了这儿,找到了机会他就反击了。我手底下十几个人,被他打伤了大半,他连把小刀都没有,还拧断了两个人脖子。他们打断他的腿,也是不得不为。”
江水眠呆呆的蹲在黑暗里一会儿,忽然好像耳鸣了,没听见旁边说了些什么。
栾老冷笑:“你带他过来是要杀他的,还不许他反抗了?我没有别的要求,你随便折腾中华武士会吧,我想要干什么都行,武林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就要他这条命。”
夏恒笑的肩膀直抖:“至于么?”
栾老:“至于。他是我第一个徒弟。我没那么有名气的时候,一碗粥就跟我走了。我们不和过,他厌恶我,我也瞧不惯他那不懂规矩不懂圆滑的样子。但我跟他当师徒的时候,西太后还在遁逃呢,你爹都还不是什么人物。我和他之前,都各自欠对方。”
夏恒没有接话,迈步往里走。江水眠连忙回过神来,栾老和夏恒进去了,宋良阁一定在仓库里,只是正门处有人还守着,她手哆哆嗦嗦的随便拿了两把刀,背上那杆春田□□,浑身叮当作响往后跑去,仓库很大,她绕了一圈,后门却没有打开,只有一个镶嵌在砖墙上的铁梯子,通往仓库顶棚。
江水眠把枪和刀全挂在后背上,爬上那道简陋的铁梯子。把手上沾了海雾,湿漉漉的打滑,也不知道是否因为精神过度紧张,几次她差点踩空。仰头看,这道台阶仿佛通往深蓝的天空和朦胧的半扇月亮似的,她几乎有一瞬间恍惚的觉得这梯子没有尽头。
然而她最终还是踩上了顶棚,很宽阔的房顶上,有两个镶嵌在顶棚上的铁窗子,大概是偶尔顶开散味道用的,今日无雨,两侧都打开着。江水眠轻手轻脚,多次差点打滑摔倒,终于爬到那开窗的顶棚前,往下望去,下头有不少木板箱子,摞的极高,她看不清到底宋良阁在哪儿,却听见了夏恒的声音。
夏恒道:“师父,你别让我难做。一个徒弟而已,他死了就死了罢。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而且他也无亲无故的,死了也不会有什么人为他伤心。我可听说过他在苏州被人叫做红鬼,身上背了这么多条人命,他早该在这种地方死了。”
栾老半天没有说话。
江水眠只看见仓库里有不少纵横交错的铁横梁,只是这些横梁都只有两只脚并起来的宽度,距离窗子也有相当一段距离。如果想从这个距离跳到横梁上,只要身子一歪,她直接掉下去,这个距离就算是没有断了脚,声音也足以让他们注意到了。
她一咬牙,就想赌一把,夏恒如果真的要杀宋良阁,她就顺着房梁溜到他身后,要不然开枪杀他;要不然就跳下来一刀毙命,看那些人还会不会在雇主都死了的时候再开枪拼命。
江水眠想着,就坐在窗沿,两只脚放下去,找准方向,心一横,往下一跳。她穿着软底的布鞋,跳下去本没有声音,然而那铁梁在海边不知道攒了多久的铁锈,铁锈居然脱落一滑,江水眠连忙抱住横梁,差点掉了下去。
她心口乱跳,只要出了一点点差错,她就是要对上好几个枪口了——
真到那时候,她的人生可没有玩错了游戏似的读档。
房梁上吊着的几个白炽灯泡嗡嗡作响,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的味道,她弓着身子,小步向前。
她听见夏恒道:“这件事情也怪你不是么?他在苏州好好地,你把他拽到天津来,掺和你的宏图大业,让他给你当枪使。你们几个,去把后门打开吧,一会儿直接把他扔海里就是了。”
几个人正走到后门去,解开锁链,把后门推开。后门就靠着港口堤坝,海味和月光一同涌了进来。
栾老:“夏恒!”
夏恒笑道:“师父,其实你在我这儿并没有什么筹码的。我说着不能杀你,却也不是真的不能杀你——”
栾老声音压低:“算我求求你……我一把年纪了,我真的不会去跟你争了,就他的命,就只有他的命!”
夏恒大笑:“师父,你要求我么?你要怎么求我,为了他,至于么?”
栾老声音发抖,又像是笑声被压在了胸口:“我这个人一向不知道什么叫要脸的。你想让我怎么求你。我他妈舔了那些军阀老爷们大半辈子了,今日不差你。”
夏恒笑嘻嘻:“那我让你跪下来求我,你也肯了?就为了这个徒弟?”
栾老一僵,心底涌出来太多片段。
西太后巡游的时候,宫家是满清最后一代大内侍卫总管,宫家随着西太后出走的时候,叫上了八卦形意不少门人前去随行护卫。栾老跟宫家有些缘分,但他本身没什么本事,自己连个像样武馆也没有,就看着宫家面子,带着当时才十二三的宋良阁也去了。、
那时候宋良阁才刚到他手底下没有几个月,瘦的皮包骨头,一路上条件越来越差,甚至有的时候连宫宝田也只有一条板凳略略一躺,宋良阁却很懂得尊师重道,什么吃的用的都会先捧给他。
宋良阁那时候就不爱多说话,却对他孝顺的很,师徒两个人穿着御赐的衣服连饭却也吃不饱。一路走,栾老就一路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