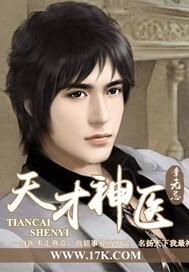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我是蒋干中记中的蒋干的作文怎么写 > 第三卷 第八十一章 出卖中(第1页)
第三卷 第八十一章 出卖中(第1页)
仲达不需相送,朝廷之事亦可先放下,君为之?骨重之处尚多,还是安心将养为佳,不可过于操劳也。”
司马懿面色蜡黄憔悴的在家仆搀扶之下,勉强吃力的往卧室门口挪了两步,微微颤抖的拱手抱拳,面露感激却声音虚弱的道:“懿多谢公子爱护之情,如今空占朝廷之位却不能为丞相、公子分忧,实汗……汗颜也。”
曹微微叹息一声,甚有感触的道:“平日有仲达左右相陪之时,尚未明觉,如今君身染病疾不能侍事,才知君之重要,故仲达之疾便如之疾,仲达之苦便如之苦也,君为之手足,手足之痛体为同受,故君切要早日康复才是。”
“公子……。”司马懿闻言激动的道了一声,便双唇颤抖着再难言语,或许人在病中,不仅是身体,就连精神心志都脆弱了许多,鹰目之中竟隐现泪光,挣脱开家仆的搀扶,双膝一软便跪了下去,以头触地浑身微颤不止。
曹见司马懿如此反应,也似乎被自己的一番言谈所感动,连忙上前在司马家仆人的帮衬下将他扶起,轻抚其臂温言道:“仲达有恙在身怎可如此?何况方才乃肺腑之言,实不能受仲达这般大礼。”
司马懿面上露出疲倦之态,却精神有些亢奋的道:“公子待我之恩,懿铭刻于心,此生难忘,然公子如此之誉懿亦惶恐,长文(陈群)长于政治,季重(吴质)善于谋划。光文(朱铄)通于人情。懿皆有不如也。”
曹点点头,这时神色已恢复了平静,自然的送开手道:“长文等人皆乃大才。亦为之心腹,然仲达却是过谦了,君已有疲态,我便不再多留,仲达只需安心养病即可。”
司马懿坚持着看曹在亲卫的护卫下离去,这才浑身如散了架般由家仆扶到卧室榻上躺下。随后吩咐家仆去请兄长司马朗,自己则闭目养神。
片刻之后,忽听卧室木门轻声一响,一青衣短须、身资轩昂,白面浓眉之中年文士悄然而入,随后司马懿睁开双眼转脸一看,虽然面色依旧暗淡,然眼中却是炯炯有神。出人意料地翻身而起,坐于榻上,尖瘦地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拱手道:“小弟有恙在身。不能相迎,还望兄长莫怪。”
这中年文士正是司马懿之兄。现任丞相主簿之职的司马朗。
司马朗神色有些无奈的笑着摇了摇头,径自来到榻边桌案后坐了,轻捋着胡须道:“仲达不过小恙,却又因何装作如此模样?莫非得弟妹相告,便连为兄都没你瞒了过去。”
司马懿淡然一笑,随后又有些感慨地轻声叹息道:“非是小弟本心,乃是不得不为也。”
司马朗知自己这弟弟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当初尚书崔>: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非子所及也”,尤其沉稳多谋、克己善忍,心性虽有些略为猜忌,但却多于权变,平日所为少有莽撞之时,因此如今这般掩饰必有深意,当下便也不客气的道:“仲达之才智非兄所及,不知请为兄前来,有何需为之事?”
司马懿与司马朗兄弟之情甚深,想当初董卓占据洛阳,以淫威凌皇帝、诸侯于上,暴虐无德,时任京兆尹的司马懿兄弟之父司马防看出天下大乱在即,洛阳、长安关中一带必遭刀兵之祸,便命长子司马朗带着比自己小八岁的司马懿及家眷逃离董卓,迁往黎阳,成功的躲避战乱,其中劳苦非外人可知,因此司马懿虽表面上与兄长不拘小结,但内心却对司马朗极为敬重,因此装病之事便不欲相瞒,另外则是有需兄长司马朗相助之处。
“此番子建公子去平河间之乱,田银、苏伯之流虽号称五万之众,却不过土鸡瓦狗一般,必不能敌,而丞相考较之意绝非如此而已,杨修即便仅有小智,然亦当可知丞相之心,若非以雷霆之势破叛匪,则难使丞相对子建公子嘉怀,且三弟叔达(司马孚)为人温厚廉让、忠贞梗直,如今既效力于公子植,又亲身随往,亦必不隐晦,而弟既从附于子恒公子,实难局中而调,故不得不退避三舍也。”
司马朗听了点了点头,眉头微簇道:“仲达之言甚是,三弟与你分置于两位公子麾下,虽不过乃是巧合,然对我司马一族却乃是好事,子建公子自幼聪慧,文才出众,然若论沉稳及军政之事却似乎稍逊于公子子恒,故先时丞相虽爱其才却恼其行,似有立长之意,不过自扬州、庐江一战后,形势似又有变,如今两公子高下难分之时,仲达实不宜轻言其间,更何况涉及三弟……。”说到此处,司马朗忽然停口不言,面上微露
色。
司马懿自然知他所思,淡然一笑道:“兄长到也不必多虑,丞相文采名动天下,虽因故喜子建公子之聪慧才学,然执掌天下者,又怎是文章了得便可之事?子恒公子军政之事更胜一筹,才乃上上之选,只观两公子身侧亲近之人,便可略明一二,丞相乃天下雄杰,自明其中优劣,此次即便子建公子能和丞相之心,日后也必难成事,然懿却担心吴季重今番施以偏锋阴谋,如此实非善事。”
司马朗闻言眉头挑起,惊骇的道:“吴质虽多智,然却常持威肆行,若果如仲达所料,绝非我司马家之福!”
见到兄长这般担忧,司马懿却从容地道:“弟之言或有过矣,有长文、光文在,子恒公子又向来谨慎,当不会贸然为险,兄长身为丞相主簿,多可见往来文书,可略为关注河间之事。”
说到此处,司马朗才完全知道了这二弟的心思,转念想到这确也符合他的性格,于是道:“仲达尽可放心,为兄必多加留意,若觉异常之处,必来告之。”
***
“季重之计虽妙,然如此未免太过无情,子建毕竟乃为之兄弟,实不当如此害之。”曹面色平静的道。
此时坐于一旁的陈群,沉稳的点了点头,双目炯然有神的道:“公子所言甚是,何况此事为之甚险,即便得成,日后亦有后患,以群之见不如静守不动为好。”
吴质听了不满的看了他一眼,轻哼一声,撇了撇薄唇道:“长文非是心善之人,平日常有恢复肉刑之言,今日怎又怜弱起来?公子念兄弟之情不肯采纳质之策,你我却不可任公子植轻得如此之功,即便不用此计,亦不可听之任之。”
曹眼见兄弟曹植有重新崛起之势,又见父亲已露偏爱之情,心中自然又恼又叹,吴质所谋虽过于阴狠,然确是好计,只不过就怕万一走漏风声,或是计谋未成,以曹植、杨修等人地聪慧,必能察觉一二,到时父亲那里……。。
“哎~”心中暗自叹息一声,曹压下>)|“光文先生以为当如何为好?”
朱铄乃是司马懿、陈群、吴质四人中年龄最长,官位最高者,如今身为中护军之职,在名位上仅次于曹植所任的中领军,乃是统率禁军的副手,因此曹对其一贯甚为尊重。
“公子。”朱向曹拱了拱手,不焦不燥的道:“铄以为长文与季重之言皆有可取之处,如今天下虽以丞相为先,然西有马、韩未灭;南有孙权、刘备窥探,北面公孙亦有叵测之心,故当同心御外为上,然子建公子渐拾丞相之喜,亦不可不虑,为此在下觉可行季重之计前半,隐讳通于田、苏二人,以使子建公子不能全功便好,如今连日阴雨,朱灵乃是惯将,必提醒公子植应需避寒雨之事,而季重身为朝歌长,正可借此时机行事。”
曹闻听沉吟片刻,心中微有不甘地点头道:“如此便如光文先生之言。”
***
我将曹植率军前去平灭河间之乱的事告予张任、陆雪二人,随后又道出心中所思,道:“干虽仅是妄断,然如今却不可不倍加谨慎。”
张任略思之后道:“家主之言赐觉甚有其理,曹操之重皆在西北、江南,昔日曾用郭奉孝之计大破乌桓,令异族皆惧,而如今鲜卑一族又彼此征伐不休,故河间及辽东等地曹军战力非强,曹植除非不欲速胜,否则必多倚重那五千中军,如此一来,恐怕在这般天气之下多会入陈留此种较大城池而驻。”
我本以为张任向来在西南,不会知道太多中原及北方之事,如今听他虽说地简略,但言语间似是甚熟,而他绝非夸夸其谈之人,因此不由感叹,真不愧是名将也!
陆雪则没想那么多,既然我这“天机”先生有了决定,又曾被我“痛骂”了一顿,因此只是淡然道:“小女听从先生吩咐便是。”
决心已定之后,傍晚时分,外面细雨连下了数天,终于有了渐弱之势,刘熙匆匆而归,顾不上稍微休息一下便赶至我们居住之处,一见我就面带焦虑的草草一礼,随后道:“先生,熙有要事相告。”
刘熙虽然年轻,但我知他向来稳重,对我尤其尊重,少有如此这般轻率之时,因此不由奇怪的皱了皱眉道:“子都有何紧急之事?干亦有事要与贤侄相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