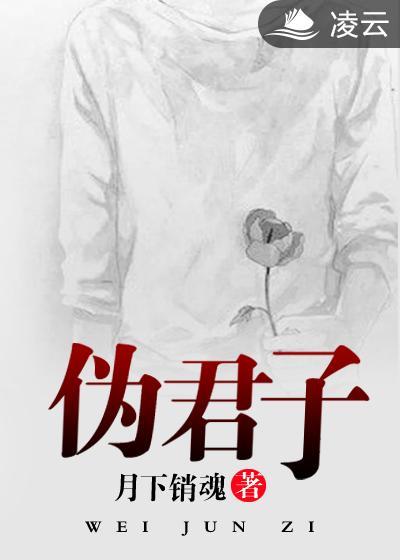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英雄无名 > 第78章(第1页)
第78章(第1页)
那就更「好看」了。我连忙门敞开,顺手扭亮电灯,瞧见墙上挂着一幅小型油画,署名「纪
曼」二字。没有错,这正是范行的别号,可是为什么出去而不锁门呢?索性坐下来等他一会,
也许是临时走出去就会回来。
等了将近一刻钟,耐不住了,写了一张便条是:「纪曼兄:来访不晤,怅甚。明晨八时
当再来,务请稍待,如有约在先,亦请留言约时一晤。」我没有写名字,因为他认识我的笔
迹。
把纸条压在桌子上,关了电灯,带上房门,循楼梯往下走,刚走到楼底下转角处,恰巧
碰见范行从外面回来。他猛然看到我,颇为惊讶,遂卽伸出双手紧握着我手不放。他问道:
「是来找我的?」我点了点头,他拉着我上楼,重又进入他的房间。
我也顾不得闲话寒喧,笫一句话就问:「你还维持着工作关系?」他回答说:「我现在是
代理『北平站』站长。上级派来张炎元先生任『北平站』区长,毛万里先生任区书记。如今
的『北平站』完全是在『北平区』指挥之下,与局本部没有直接关系了。据我所知,除我一
人之外,还有一个在北长街看门的老尹,其它的都调走了。」
我又问他:「离开北平的那些人,目前的景况怎样了?」范行说:「我不完全清楚,耳闻,
白世维和王云孙正在受训,戚南谱已另派工作,不在华北;杨英调去天津电信局;王文和那
个姓刘的,仍在禁闭中。还有嫂夫人在一处接受优待,只是不能自由活动而已。」
我听罢范行所说的这番话,已大致明白了他们的概况。接着又半真半假试探着问他:「我
现在来看你,完全是私人行为,基于你的职责,该怎么办?」他听后愕然,大惑不解的说:
「怎么办?老大哥你还不信任我,我们的关系不同,无论如何我也不会不够朋友,而何况你
也没有犯下什么不可赦的滔天大罪。」
范行非常关切我今天后的动止和意向,他劝我宜于早日澄清此事。当然,他也拿不出一
个好办法来。我坦率的对他说:「我来此的目的,是在打听消息、了解情况,在没有澈底弄
清楚之前,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范行善意的提出:「老大哥你没有考虑过直截了当的去南京见戴先生?我想经过解释后,
他会谅解的。」我毫不掩饰的说:「这件有失体面的事,的确是我处置失当,除了愧对于戴先
生之外,我对他实在有点怕,如果说是畏罪,我也并不否认。所以我想等到情势淡化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