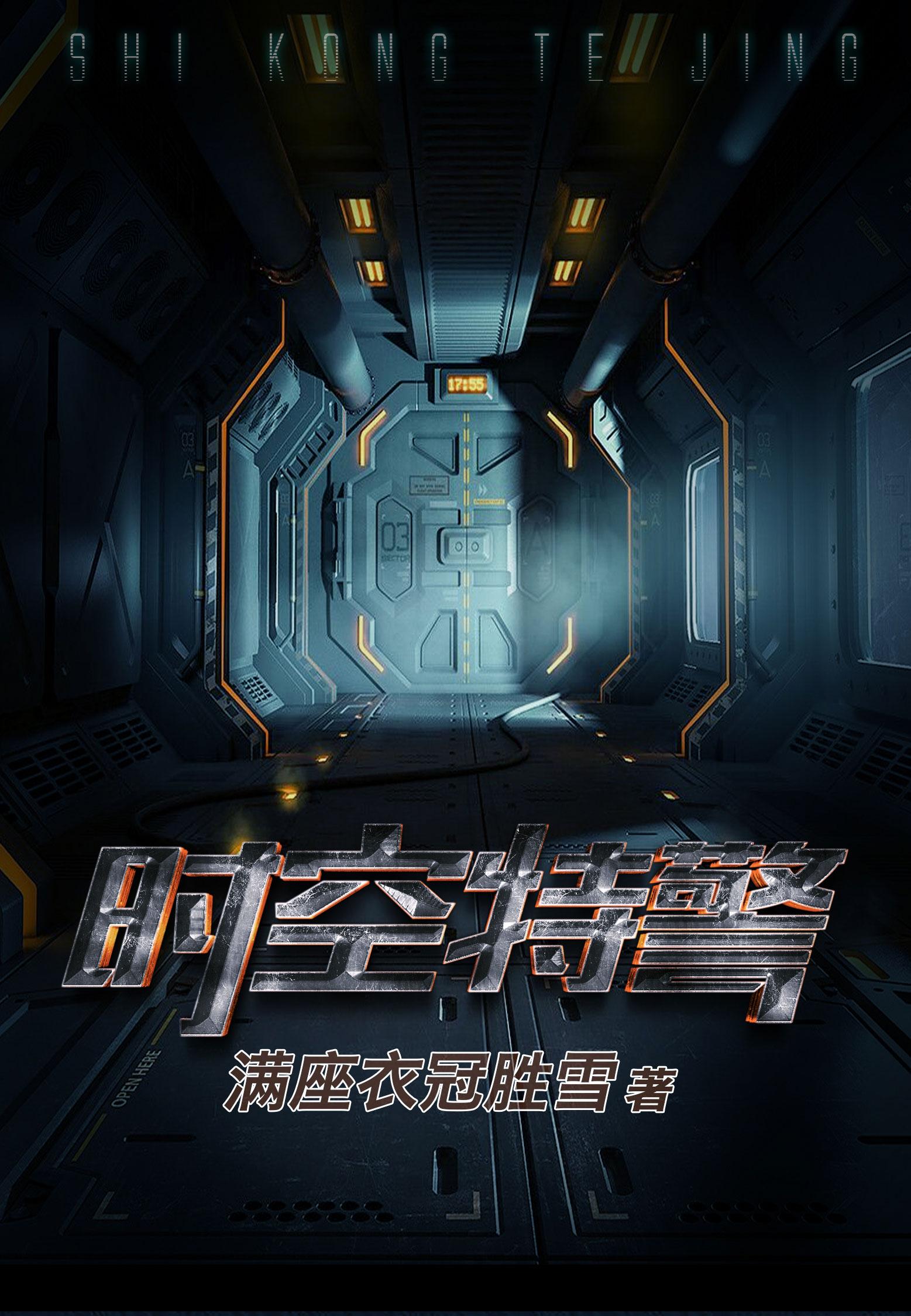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许你星河千里by桃桃一轮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泥撕挂皮。”(你是傻子)
巴云野故作虚心求教,“什么意思?”
刁琢转头看她,她轮廓深刻,美得犀利,上挑的眉形为她增添几分侠客风情。日喀则检查站查身份证时,他看过她的身份证,云南人。
“夸你漂亮。”
巴云野冷笑,“以为我没带过陕西客人?——要饿社,逆才撕挂皮!(要我说,你才是傻子)”
刁琢向她伸出大拇指,话学得九分像。相处这几天,他发现她各地方言都会一点,看来有点语言天赋。
沿路都是动物风干的尸骨,大大小小,七零八落,有的整具出现,有的只留一两根粗壮的大骨,有的看似年代久远,好像一碰就会化成粉末。死亡禁地与天堂美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毫无违和感。
“下雪了。”刁琢远远望见,前方一片雪白。不多时,细细的雪花飘下,伴随十级的大风,冷箭一样向车队扫射而来。天空一片浑浊的白,远处似乎还有什么不寻常的响声。
“不好……”巴云野喃喃道。
刁琢眉头紧皱,也嗅到极端气候的味道。
果然,前进没多远,就看见远方山体已经被一片土黄的沙幕笼罩。暴雪居然夹杂着沙尘暴席卷而来,杀得人措手不及。
“不能再往前,得找个能避风的。”巴云野一把抓起对讲机提醒后车,“小心!沙尘暴来了!!”
暴雪和沙暴进行的速度极快,不一会儿,所见之处都是一片浑浊的土黄,沙尘蒙蔽阳光,像死神张开的双手,狠狠向万物扑来。
避风处一时难寻,车队只能就地停下,所有人呆在车内,噤若寒蝉。狂风呼啸而至,无数砂粒撞击在挡风玻璃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风似乎还不满足,以雷霆万钧之势,几乎要将所有车子吹翻。沙尘包围了天地,车内一片昏黑,世界末日一般的视觉感,加上时不时被狂风掀起往另一侧倾斜的车体,让人不由得怀疑自己能否活下去。
自然的力量在羌塘格外凶猛,如同鞭子一样一下一下抽过狂妄的人类。任你楼宇参天,任你大数据云计算,到了这里,你就是生物金字塔较低的一层,除了随时沦为野兽的盘中餐,还有可能在狂风暴雪之下毫无还手之力,另外,更可怕的未知力量也不知在哪一处等着你。它要教会你什么叫原始的恐惧,自然永远不会被征服,它是该被人类高高供起来的神!
“我他妈敬邹开贵是条汉子。”巴云野在沉默地坐了十分钟后,忽然吐出一句话,“徒步的时候碰见这种天气,你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吹到哪儿去,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头和屁股分别被吹到东还是南。”
刁琢虚望着黄沙漫天,“他不一定碰见这个。”
“你听过关于羌塘的其他几个失踪故事吗?”
“说说看。”
“以前有个外国的探险队组织徒步穿越羌塘失踪,几年后被发现其中几个人死在一个离他们计划路线的超级远地方,过了几年,剩下的人又出现在上几个人被发现的地方,但这个探险队的所有人其实死亡时间都差不多。就好像什么人在他们全死光后,分两批把他们运到同一个地方似的。”
反正外头沙暴不停,车子也无法移动,巴云野干脆打开话匣子。
“还有个车队,三四辆越野,开进去也没再出来。找到的时候车还在,性能什么的都正常,水、食物还有剩,人全没了。前几年,我还听说有几个男的徒步,推着车,后来也是车子被其他穿越者找着,吃的都在,人和一些通讯设备不见了。放弃车子和食物只身穿越是不可能的,不知道他们经历了啥。”
“这些人的尸体,后来出现没有?”
“找不到。”巴云野说,“网上有人分析,徒步的那几个人有可能是遇见狼或者即将冬眠的熊,被拖走吃掉,但那几个开车进来的怎么会人间蒸发,谁都说不出所以然。就算遇见低温、沙暴或者野兽,无论如何躲在车里也比出去强。”
巴云野想起在玉珠峰神秘失踪的张晨光,他丢下背包,又去了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玉珠峰那种入门级的雪山,每年登顶的人不在少数,为什么就是没有一个人再找到关于张晨光的什么物品?
他该不会装死,其实逃到哪里躲起来吧?或者,被人抓走了?
外头仍然狂风肆虐,她百无聊赖地套上u型枕,歪着脑袋忙着剪辑这两天拍的小视频,弄着弄着昏昏欲睡。
刁琢撑着方向盘,转头刚要跟她说什么,就见她闭着眼睛,十分安静地打瞌睡。他移开目光,但一会儿后又转头望着她。
跟其他白得像雪或者粉底涂得跟墙皮似的女人不同,她皮肤偏蜜色,平日里爱用魔术头巾把自己的脸、耳朵、脖子包得严严实实,再戴一副黑墨镜,美帅美帅的。这下子不小心睡着,忘了拉上魔术头巾,姣美的五官明朗清晰,长而浓密的睫毛随着呼吸频率轻轻颤动,又好像随时都会醒来,机灵又戏谑地打量你。
他的目光移到她的唇上。
这里是不是跟她的手一样柔软?
妈的,她要是时时刻刻像睡着是这样恬静柔顺就好了。
刁琢靠在另一侧闭目养神,车载音响恰好播放一首曲调安静的歌。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
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