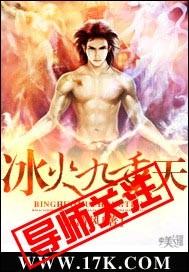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红线椒图片 > 第17章(第1页)
第17章(第1页)
&ldo;苏&rdo;苏卿鱼手中的书摔落在地上。
姑姑,竟然是姑姑。
苏卿鱼清楚地读到了那个名字,没有错的,就算同名同姓,未免也有点太巧?这么多年的思念牵挂,还有那个一直没有得到答案的问题,就这样曲终人散了?
苏卿鱼不相信,她三步并作两步,把一楼的每个房门都推开,只见里面书报整齐,仿佛办公人员明天还要来上班,而不是几十年前就遗弃了这段历史。
冲上二楼,苏卿鱼又逐个推开病舍房门,里面也是被褥齐全,仿佛等待病人入住。终于,她在走廊最右侧的尽头发现了那扇包着皮革的大门,门口铜牌树立:标本展览室,无关人员请勿进入。
推开沉重的大门,屋里是怎样一幅景象。每个架子上都堆满了密封玻璃瓶,其中各种器官无奇不有,一排各个发育时期的胎儿标本更是乍眼。这些浮在水中的&ldo;零件&rdo;,竟好像也分享了生命的一部分,在死后还要注视着不期的来客。
苏卿鱼的目光锁定了靠窗一排被披上白布的等人高物事,没有犹豫,一手掀开了左手第一张白布,一具保存完好的白骨就藏在白布之后,直勾勾的盯着她。这是姑姑吗?姑姑比这高些还是矮些?苏卿鱼却不知道答案,对于一个思念甚深的人,苏卿鱼的了解却是少得可笑。
掀开第二张白布,一具被剥了皮的尸体立在那里,每一丝肌肉纹理,每一根浮现在皮肤之后的血管都被完美的塑化,展现出人体赤裸裸的血腥。苏卿鱼扭头干呕几声,随之又掀开第三张白布,还是一具塑化人体,胸腔却被剖开,只剩一层似有若无的胸膜,五脏六腑空荡荡的吊在肋骨后面,好像还保持着生时的模样。
哪个是姑姑,哪个是姑姑?苏卿鱼就像一个马拉松选手一样在期盼着终点的到来。这注定是一场忍耐折磨的比赛,选手们都以为自己为光荣而跑,享受过程的快感,踏上旅途之后才发现真正期待的只有终点。苏卿鱼却不得不逐渐放弃寻找终点的希望,谁又能确定姑姑一定还留在这里而不是藏在哪个博物馆里,就算确定又怎么能判断哪一个才是,就算断定又于事何补?
苏卿鱼毅然掀开第四具也是最后一具遗体上的白布,然后答案出现在眼前。
没有错,那是姑姑。姑姑和记忆力一样年轻。一定是医生也不忍心剥了这么美丽的女子的皮,于是让她留住了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姑姑好像蜡人一样冲着空气微笑。
苏卿鱼不记得是怎样走出标本陈列室,怎样走出小楼,怎样穿过坟地,怎样找到归路。只记得恍恍惚惚间已经走上了回家的小路。她的一生从没有如此沉重过,因为想找的都一定能找到,没找到的也都坚信着未来一定可以寻见。却只有这一次,一个十年的梦想,在一夜间破灭。胸口上一块大石忽的消失无踪,以为会松上一口气,谁知却是没头没尾的空虚。
走进家门,两个室友破天荒的坐在客厅,而表针已经走到了午夜十二点,平时三人早已各归各屋准备睡觉了。苏卿鱼没精神理会她们,自顾自坐在沙发上脱衣换鞋,一抬眼才发现两人还在那里呆坐着,直勾勾的看着她。
&ldo;小鲫鱼,&rdo;两人喊着苏卿鱼的外号,吞吞吐吐的站起来坐到沙发上,一左一右抱住她:&ldo;有个坏消息,但你一定要答应我们坚强起来,不管什么时候我们都会在你身边陪你渡过难关的。&rdo;
苏卿鱼愣了愣,想开口问却发不出声音,她真的不想再要坏消息了,可不可以等过了今晚,明天再告诉我?
室友看她不吭声,对望了一眼只好继续开口:&ldo;你家里今天打电话过来了,我接的。你爸妈你家的楼煤气爆炸了,你爸妈没抢救过来,家里人问你要不要回去看看?&rdo;
苏卿鱼一时间脑子里失去了所有的概念,不知道是该哭好呢,还是要问&ldo;怎么可能&rdo;。走吧,走吧,凭什么非要做出反应?睡吧,睡吧,多大的事都明天再说。
苏卿鱼没再理会室友的殷勤安慰,径直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灯,反锁房门,站在屋中间不知该如何是好。敲门声响了一会也就不响了。一天之内,怎么丢了那么多?苏卿鱼不明白也不愿意想,不如自己也一觉睡过去,永远不醒来该有多好。
&ldo;嘀哒!嘀嗒!&rdo;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滴水声。不管它,苏卿鱼掀开被子,想一头躲进去不再出来。
可惜有人已经捷足先登,连这么一点小小的愿望都不让她实现。被子下面是小黑猫土豆和她的妈妈,身首异处,四肢被摆出两个可笑的造型,它们的血一直往下滴,一直流到了苏卿鱼的脚边。
12夜比梦长
等太阳晒屁股了苏卿鱼才醒。一睁眼就被太阳晃得赶紧闭上,眨巴了一会儿才发现自己正躺在坟场黄土地上,头还枕着一块倒了的墓碑。
最后的记忆明明是在公寓里,怎么又睡到坟场来了?苏卿鱼琢磨不透,但也隐隐觉得不妥,赶紧往家奔。天一亮了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其实只是一片空地,要想找到路还不容易吗。远远看到昨天晚上闯进去的小楼,苏卿鱼略微犹豫了一下,没理会。就这么连跑带颠的,不到二十分钟已经走到家门口。门没锁,一拧就开,一进门就看到室友正在客厅吃早饭。
&ldo;嚯,你还知道回来啊!&rdo;室友一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