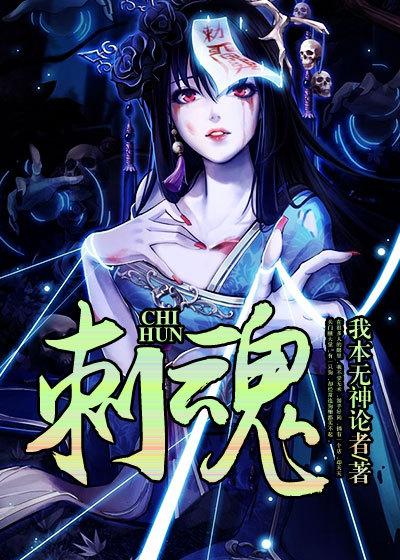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窦公公的小傻子免费阅读无弹窗 > 第71章(第1页)
第71章(第1页)
窦贵生正要说求见就求见吧,慌什么慌,便见小太监抖着双唇抬起头:“他在院外跪下了,求圣上查明真相,不可滥杀无辜。”
窦贵生心头一跳,自早上起心头笼罩的不安顷刻间如同黑云压城般席卷而来。他怔了片刻,急匆匆往外跑,甚至忘了跟靳乔告辞:“快,人呢!”
就在院外头,方才不是说了嘛。小太监咽下反驳的话,领着火急火燎的老太监冲了出去。
人跪得凄凄婉婉,飘飘摇摇,乍一看去,仿佛跟当初跪在司礼监门口的人影融为了一体。每踏出一步,窦贵生紧绷的神经就狠狠颤动一下,直到走到人前,见到十六皇子通红的眼眶时,那根神经终于不堪重负地崩断了。
“窦公公,”十六皇子死死攥住他的手,声音仿佛被人扼住了喉咙,“救救小白……你救救她!”
心跳陡然停顿,窦贵生险些仰面倒下,幸亏有小太监在身后托了一把。
“殿下不必心急。”他稳住声音,不知道是在安慰对方还是安慰自己,“……怎么回事?”
十六皇子双唇血色尽失,声音同面色一样挫败:“方才江如去了莫啼院,说那日的毒酒是小白倒的,把小白带走了……刑部查验了席间所有酒具器皿,只有小白的杯壁外沾了毒。”
十六皇子不知道刑部抽丝剥茧的推断,不知道酒液是如何从壶里洒出来,如何沾到鹿白手上,又是如何留在她的杯壁。他如同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苦苦哀求道:“我知道不是她,她闲来无事杀太子做什么!你能不能……能不能跟父亲求求情?”
短短几秒内,种种猜测如同喷发的岩浆般争先恐后射出,在窦贵生心上烧出无数滚烫的洞。
对,是九皇子。此举一箭双雕,既能杀了太子,又能除掉鹿白。皇帝坐享其成,正好有机会叫宝贝儿子登上太子宝座,压根不会理会真凶是谁。至于自称是亲爹的吴玉呢?正好,一起办了。
当然,也可能是吴玉。老匹夫深不可测,表面维护东宫正统,私底下却跟九皇子搅成一团,就是个实打实的墙头草。大势所趋,太子那里是换不来任何好处了,保不齐老匹夫会先下手为强,以此胁迫皇帝和未来的皇帝做出让步,强行把他们拉到同一根绳上。
丞相之上,还可再进一步。
除此之外,有没有那么一种可能,即鹿白的单纯莽撞全是伪装,实则她就是个包藏祸心、无恶不作的黑心莲呢?
窦贵生对产生这等想法的自己讥笑一声。怎么可能,她哪有那个脑子?
十六皇子哽咽着哭诉:“江如要把人交给刑部,说不定还要砍头。就算、就算不砍头,入了大狱都得先受刑,小白她……她受得住吗?”
“什么时候的事?”窦贵生缓缓跪坐在十六皇子身旁,声音温柔缱绻,如同安抚稚儿的母亲。
“有半个时辰了。”一滴眼泪顺着低垂的鼻尖滚落在地,啪嗒碎裂,水光四溅,一如十六皇子同样不堪一击的爱情。
“芳姑怕我着急,一直没说。甄秋告诉我时……人已经被带走了。”
“不必心急。殿下回去等着吧。”窦贵生轻声重复了一遍,“她命大着呢。”
他的脊背挺得很直,如同一根迎风而立、坚韧不灭的红烛。烛火在白石宫道上渐行渐远,烧得很沉默,很平稳,
十六皇子想问,却没有问:你怎么一点都不急,你当真不喜欢她吗?
同样地,窦贵生也没有开口:若我能救她出来,你会不会永远待她这么好?
窦贵生并不急。他把自己的慌乱情绪挖了个深坑埋起来,用树枝和落叶盖好,覆上土,在上头踩了几脚,便装作如履平地,无所畏惧。
不过是些沉疴旧怨,他安慰自己道,在后宫浸淫了这么多年,在太子和九皇子间周旋了无数回合,只要心不乱,就保准不会出错。
然而,事件发展远比他想象得更严重。先从皇帝家事变成了国事,又从国事变成了国际大事。
主理此案的是刑部崔侍郎。此人母亲是皇商,父亲是已故太傅,家中又富又贵,又有权又有钱。犯不着巴结媚上,犯不着送钱送礼,且性情古怪,孤高固执,因此与谁都无甚来往,连丞相吴玉都不放在眼里。
皇帝心知此事蹊跷,唯恐这个死脑筋查出什么,坚决不同意由他主理,但耐不住朝臣坚持,吴玉坚持,就连九皇子都信誓旦旦,泪洒大殿:“流言可畏,圣上定要还我清白!”
这声生疏至极的“圣上”叫得皇帝心口酸疼,他只能妥协。
按照程序,入了刑部大狱先有一道“迎门礼”,甭管有没有罪,进来先杀了你的威风再说。倒不是什么酷刑,只是打屁股而已。
又是打屁股。鹿白被按到刑凳上,甚至有些暗自窃喜。这回不用扒裤子,甚好。
刑部的狱吏可不是典刑司娇娇弱弱的小太监。打第一棍的时候,鹿白皱了眉,别说,还真有点疼。打第二棍的时候,她下意识抬手捂,才想起手被人牢牢按住了。打到第五棍,疼痛和麻木沿着坐骨神经飞快地蔓延,瞬间侵占了下半身。
打完十棍,鹿白前胸后背已经湿透了。
狱吏把她拖到牢里,扔了包黏腻、腥臭的药膏过来:“好生擦,没使多大劲儿。”
鹿白趴了半晌,才呲牙咧嘴地爬起来:“这叫没使多大劲儿?我打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