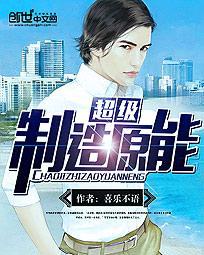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入幕之兵苏眠说txt百度 > 第8章(第2页)
第8章(第2页)
好像是一句感慨,却被她用轻松的语气说了出来,在那坦荡荡的眼眸里,秦赐甚至看不见更多的情绪。
他低哑地道:&ldo;我自然想跟着您。&rdo;
秦束笑着,没有再说了。
他可能还分辨不清楚,但她已经明白了。
他是相信她的。
而在这世上,如果还有永不背叛的感情,那她也只能相信他,只肯相信他了。
&ldo;你啊,不能跟着我进宫。&rdo;秦束站起身来,&ldo;你要去军中,做一番事业,再来见我。&rdo;
半月后,秦束带秦赐去了洛阳城西的军屯。
&ldo;你无门无品,本该从疆埸上得功名。&rdo;马车停在了军营辕门外,秦束拂开车帘,对秦赐微微一笑,&ldo;在这里历练历练,多则三年,少则一年,想必便有拔擢的机会了。&rdo;
夏日的太阳已很盛了,秦束微微眯了眼,复笑,&ldo;在军中也不可忘了读书习字,有事便给我写信。&rdo;
秦赐没有答话。在日头底下,他穿了一身戎装,是秦束特去城中挑选了布匹,就着父亲的旧衣改作的。在闺房的灯下,她忙碌了三个晚上,才草草将这件衣裳做成,她望着他,劲装结束,倒也是挺拔英武;若是升了品秩,朝廷便自然要发下更好的衣装……
她不知自己为什么会想那么多。
&ldo;娘子。&rdo;秦赐忽然道。
&ldo;嗯?&rdo;秦束回过神来。
&ldo;……&rdo;
直到最后,秦赐什么也没能说出口。
也许是什么都来不及想,也许是所想的已然太多,全数挤在喉咙口,到了尽四散了。
那双浅灰色的狼一般的瞳仁里,有些怨恨,有些留恋,有些迷惑,有些不甘,秦束都读出来了,可是秦束也不能径自作答。
她只能笑,&ldo;保重。&rdo;说完,那车帘便哗啦落了下来,再片刻,马车便起行了。
许是阳光太盛,车轮竟尔卷起了尘土。一声低低的嘶鸣,秦赐转过头,是那匹黑色瘦马,正低垂脖颈蹭了蹭他的甲衣。马鞍边挂着一个简单的包袱,他不像那些高门大户送来从军的郎君们,没有那么多行李可带,便这一个包袱,也是秦束给他置办的。
他伸手摸了摸瘦马的耳朵,那马耳朵便抖了一抖。
&ldo;娘子,&rdo;马车之中,阿摇一边给秦束打着扇,一边忧虑地道,&ldo;这京畿的屯军里,要么是骄横的世家子,要么是不讲理的胡虏,您就不怕他过不了这关么?&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