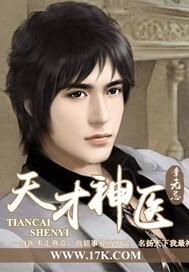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他是一个小结巴虞渊百度 > 第28页(第1页)
第28页(第1页)
霍扬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向他露出一个微笑来,很礼貌地切断了这个话题:“谢谢你今天做的饭。”“不是,我真的没有……”阮秋想把话说完,他越是着急便越是气喘吁吁的,话便说得更不利索了,但真的等霍扬安静下来,用一双平静的眼睛看着自己时,阮秋又怯了场,一肚子想说的话就这样梗在喉咙里,“我……”霍扬唇角动了一下,似乎是个笑,但眼睛里却是冷的:“没事的话你就先回吧。”一直想从这里离开的阮秋却又怎么样都拔不动自己的腿了。他总觉得自己该说些什么,可是喉咙里却像是塞了一团棉花一样说不出来。他想问问霍扬明天有没有什么想吃的,或者是再次解释自己对于霍蔓并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可是阮秋踌躇了半天,最终也没能张开口。霍扬瞥了他一眼,像是诧异他怎么还不走。片刻后,他想起来什么,很轻地笑了一声:“哦,差点忘了。”阮秋茫然地看着他,只见霍扬拉开一边的抽屉,随手从里面拿出一个皮夹来。他当着阮秋的面,打开皮夹,很随意地从那些崭新的纸钞里点出三张来,推到阮秋面前,露出一个有些让人发冷的微笑来:“还有其他事吗?”阮秋只觉得遍体生寒。他紧紧地咬着唇,顶着霍扬冷漠视线的打量,小心翼翼地低声开口:“那、那明天、你有什么想吃的吗?”“……”霍扬沉默地看着阮秋,声音很冷淡道,“明天她也有事,也不会来这里。”他特意加了重音,像是强调这一点一样,“之后直到我离开这里,她都不会来。”阮秋愣愣地看着霍扬,像是完全没反应过来:“哦……”“如果你不想来,我也可以换其他人来照顾我。”霍扬冷淡道,“我不是非你不可,你明白吗?”阮秋虽然不懂霍扬为什么突然说起这些奇怪的话来,但他确实知道,霍扬勾勾手指,就凭着他身后的霍家,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不求薪酬也愿意来照顾他。阮秋想了一会,老实地开口:“好……所以、明天吃什么?”“……”霍扬绷紧的身体松了下来。他看着懵懵懂懂看着自己的阮秋,叹了口气,似乎带着些无可奈何的意味,“我都可以。”阮秋虽然对于这个突发的小插曲虽然颇感古怪,但是在金钱和霍扬的双重“诱惑”下,他依然每天都奔波于打印店和医院两头,以至于阿婆看着每日早出晚归的阮秋,不由得心疼地劝起他来:“小秋啊,身体才是最要紧的。”阮秋拿着毛巾揉搓着自己的短发,对上镜子里自己眼下有些泛青的眼圈,用手指轻轻揉了揉,仿佛这样就能让黑眼圈消失似的,然后朝着阿婆露出一个笑来:“我、我没关系的。”阮秋并没有撒谎。他其实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从旧巷子来到这座北方城市的时候,那时候的每一天都比现在还要辛苦。他在嘈杂的市场隔间里睁开眼,掀开帘子看见的是杀鱼的夫妇一地的血水与那些密密麻麻的鳞片。他记不清自己到底打过多少份零工,一天要在这座小城里辗转多久,只记得那时候自己的鞋是很容易穿坏的。他捏着票子站在批发处理的地摊上,买最便宜的鞋,晚上在临时搭建的棚里入睡时,在民工熟睡到震天的鼾声里,他在昏黄的电灯泡下,才看到疼痛到麻木的脚上是触目惊心的血泡。他吃了教训不敢再买廉价的鞋,因为省下的这些钱反而浪费了他更多的时间。他瘦弱,没有其他人那样使不完的力气,便尽可能地做得更好。他晚上入睡并没有那么困难,往往是一天做得太累,梦里大部分时候都是一片空白,偶尔才会做一些阮秋连想都不敢想的梦。他习惯吃苦,习惯受累。也习惯在他人白眼里讨生活。他觉得挺好的,这个世界还愿意给他留一扇窗户,给他留一个做美梦的夜晚,教他如何在梦里弥补那些痛苦。阮秋早就习惯了。只是到现在唯一还不能习惯的,是与他从前三年生活里突然偏轨、突然闯进自己人生里的霍扬。他感觉自己的一切努力在霍扬的面前,就好像彻底清了零。阮秋总以为自己已经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人,他已经开始赚钱,已经开始履行阿婆将自己捡回家,他坐在阿婆脏兮兮的躺椅上郑重许下要给阿婆养老的誓言。可是看到霍扬的时候,他便总能想起无数个夏夜里,有一双宽大的手掌,牵着他,闯进芦苇荡。那时候的水真的很清澈啊。阮秋想,栓在岸边的木船,藏在霍扬手里原本盛着金平糖现在盛着萤火虫的透明瓶罐,和天上一弯皎洁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