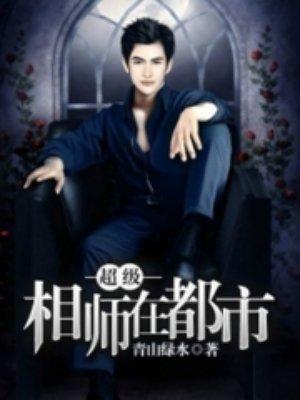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天才锁匠优美词汇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所有的人都要我这样,每个人都是。相信我,他们什么都办不到。
每次去看过不同的医生,利托大伯就会得到不同的诊断,在回家路上还会说给自己听:&ldo;选择性缄默症&rdo;、&ldo;心因性失语症&rdo;、&ldo;创伤导致喉头麻痹&rdo;……到最后,全部都差不多。不管是什么原因,我就是决定不说话了。
只要别人知道我在卖酒的小店长大,就会问我被抢过几次。每次都是这样,绝无例外,这就是一般人问我的第一个问题。答案是‐‐只有一次。
那是我搬去跟大伯住的第一年,一个夏天温暖的夜晚,停车场空荡荡的,只剩下大伯的双色水星马奎斯轿车,车后面的保险杠还撞凹了一块。
那个人走进店里,很快绕了一圈,确定店里一个客人也没有。他停下脚步,看到我站在通往后面的走廊。坦白说,当时我确实不应该在店里。我才九岁,而这家店卖酒。可是利托大伯也别无选择,起码晚上只能这样。我多半乖乖坐在后头的房间里,那是我的&ldo;办公室&rdo;,利托大伯是这样说的。四周堆满装酒的纸箱,大概有五尺高,还有一盏台灯。我每天晚上就坐在那里看我的漫画书。那些书多半是从街角的商店买来的,每天都这样,看到要回家睡觉的时候。
就算我当时不应该在那里出现好了,可是我还是每晚都在。城里每个人都知道我的事,也知道大伯已经尽力养我了,完全不靠别人帮忙,所以大家都不打扰我们。
那个人站在那边好久,低头打量我。他脸上长满雀斑,还有一头颜色不深的红头发。
&ldo;老兄,需要什么吗?&rdo;利托大伯的声音从柜台传来。
那人什么都没说,只对我点个头就离开了,就在那一刻,我知道他身上有枪。
关于这一点你得相信我,虽然我只有九岁,可是我就是知道。你大概觉得,我现在是事后回想才这么说,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所以自然以为自己知道结果,纯粹是回忆作祟。可是我对天发誓,就算时光在那一刻停止,我也可以告诉你接下来会怎样‐‐他会走到前面去,右手拿枪指着利托大伯的头,让他把收银机里的钱都交出去,就像漫画里的情节一样。
一等那人转身,我就关上门。后面房间里有电话,我过去拿起话筒拨了报案电话,响了两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ldo;你好,有紧急事件吗?&rdo;
紧急事件‐‐或许只有这样才行,说不定这样我就能开口说话了,等到必须说的时候,自然会说出口。
&ldo;喂?听得到吗?需要帮忙吗?&rdo;
我紧紧抓着话筒,什么都说不出来,我知道自己是不可能说话的。这我很确定,不过当下也注意到其他的事‐‐恐惧,那种我每分每秒都感受的恐惧,就在那一刻全部消失了,一点都不剩,起码当时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几分钟,是我第一次一点都不害怕,尤其是经过六月那件事以后,于是我决定要做下一步。
接线员还在讲话,我由着话筒掉下去,在电话线的一头晃荡,声音也变成听不清楚的嗡嗡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报案这样就够了。只要打过去,接通了不挂断,警方就会追查。不过在这天晚上,等警察找到这里来,恐怕也已经太晚了。
我打开门,走进店里,隔着长长的货架,我听到一个急促尖锐的声音在说话。
&ldo;没错,全部都要,全部的钱都放进去,就是现在。&rdo;
利托大伯的声音低了八度,&ldo;老兄,放轻松,没人会做傻事。&rdo;
&ldo;那小鬼在后面干吗?他要去哪里?&rdo;
&ldo;你别管了,他跟这里没关系!&rdo;
&ldo;把他叫过来好了!我现在很紧张,你总不希望我紧张失手吧?&rdo;
&ldo;就算我叫也没用,他听不见,他又聋又哑,你放过他就是了!&rdo;
这时我从转角走出来,看到他们两个。我还清楚记得当时的景象,每个细节我都记得。利托大伯手里拿着纸袋,另一手拿着收银机里的钞票。他背后是展示用的酒瓶,柜台上还有咖啡空罐贴着我的相片,上面还贴着一张纸条,要大家捐钱帮助&ldo;奇迹男孩&rdo;。
另外那个人‐‐那个抢匪,就站在那里,右手握枪,一把左轮手枪在霓虹灯的映照下发光。他很害怕,这我看得很明白。一枪在手,照理说应该是什么都不怕,掌控情势,结果却刚好相反。那个人怕到无法思考,对我来说,这是再好不过的情境教育,虽然我那时候才九岁,那一幕我却会一辈子记得。
抢匪打量我两秒,在下一秒拿枪对着我。
&ldo;麦可!&rdo;大伯吼道,&ldo;该死的快走开啊!&rdo;
&ldo;我以为你说他听不见。&rdo;抢匪说。他走过来抓住我的衣服,我立刻感觉到头上抵着一把枪。
&ldo;你在干吗?&rdo;大伯质问,&ldo;我不是说会照你说的做吗?&rdo;
抢匪的手在抖。大伯脸色惨白,两手前伸,好像想把我拉开,拉到旁边。我不知道当下他们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害怕。不过我说过了,我自己倒是一点也不怕。或许会怕其实是优势,毕竟总是有其实要害怕的时候,突然间应该要怕了,却没什么感觉,确实不是好事。
大伯颤抖的手把收银机的钞票塞进纸袋里。&ldo;全拿去!&rdo;他对抢匪说,&ldo;看在老天分上,拿走就快滚!&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