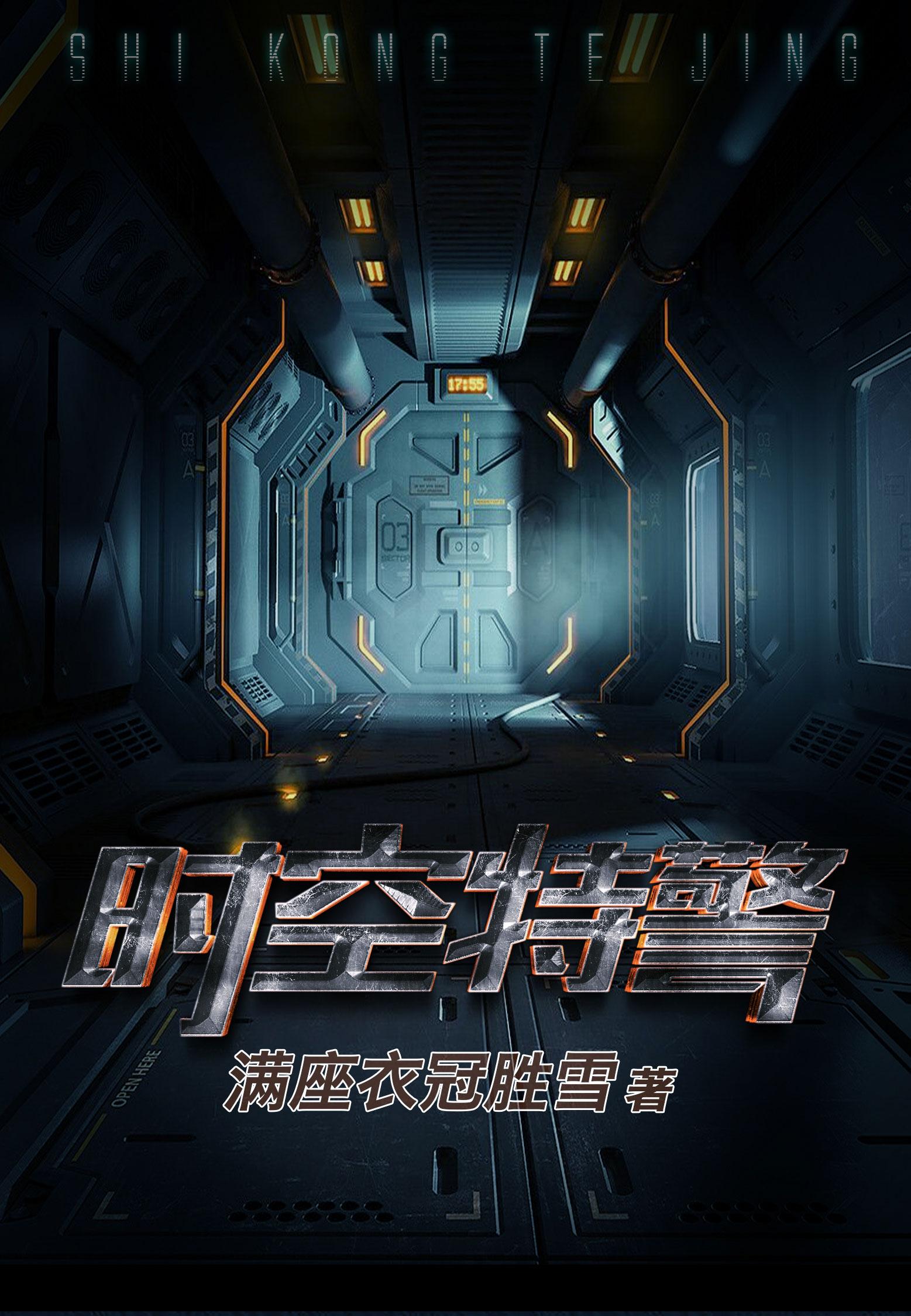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爱情万岁电影简介剧情 > 第151章(第1页)
第151章(第1页)
为自己而活,这话打动了方子衿。她也想享受一下为自己而活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给女儿打过电话,她突然很想听一听白长山的声音,要了一个白河长途。可是她的运气不好,白长山没有上班。他的同事说,白长山最近在办离休手续,不来上班了。放下电话,方子衿怅然若失。白长山想提前离休的事,她是知道的。对家庭,他已经陷入绝望,对工作,他也是没有了半点兴趣。他在信中说,既然国家有规定,他这种资历的人可以提前离休,而且离休工资丝毫不少,他也不想再争什么了,这一生,就这样结束算了。当时,方子衿还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现在得知他真的付诸行动,仿佛看到了他那颗死灰一般的心。她的心仿佛被一根绳子套着,那根绳子猛地搅动起来,将她越套越紧,有节奏的阵痛,令她几乎虚脱。
卢瑞国是第三天回来的,听说方子衿住在地委招待所,当晚就到招待所和她相见。她向卢瑞国介绍情况,卢瑞国摆了摆手说,你不用介绍,所有的情况,我都清楚。方子衿瞪大了眼睛,说,你有千里眼?卢瑞国笑笑说,我毕竟是从那里出来的,那里有任何风吹糙动,都会有人告诉我。方子衿哦了一声,说,那么我到地区的事,你也是早就知道了?卢瑞国再次笑笑,说,把东西拿出来吧,我现在就给你签字。方子衿拿出那份报告,卢瑞国掏出笔,在上面龙飞凤舞签上自己的名字。方子衿拿过那份报告,盯着那三个字发呆。难怪人们那么热衷于权力,权力真是个好东西,有些人千辛万苦得不到的东西,有人却只要轻飘飘写出自己的名字,立即就解决了。
卢瑞国指着报告说,你明天去找办公室盖个章,再到计财处盖个章,然后你把报告拿在手上。记住,千万不要留在办公室或者计财处。方子衿不解。卢瑞国更进一步说,你如果留给他们,他们就会直接通知县里。县里拿到这份报告,还替不替你办事,谁说得清楚?我的名签了,公章盖了,他们可以拿到钱了。如果他们卑鄙的话,把你抛开,我再没有办法帮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自己抓着这份报告。你也不用找他们了,你人还没有回去,他们肯定已经知道,让他们拿着你要的东西来找你。
回到医院,已经有人等着她。对方自我介绍说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受肖县长之命,来拿报告的。方子衿心想,幸亏卢瑞国提醒,不然自己说不准还真的上当了。她说,好哇,我要的东西带来了吗?办公室主任莫名其妙,说你要的东西?么东西?肖县长没告诉我呀。方子衿说,那你就回去问他吧,问清楚了再来找我。
从那天开始,那些人便天天来磨她,找出各种理由。诸如办手续需要时间修路不能等之类。最荒唐的是医院有一个熟人找到她,提出以一万元买走她手上的报告。这样一闹,闹过了十天,报告仍然在方子衿的手中。方子衿想,自己是不是该给卢瑞国打个电话,问问他该怎么办?转而一想,卢瑞国肯签上自己的名字,已经是帮了她的大忙,剩下的事,自然是她自己去做了,如果连这点事都做不好,自己还有脸去找人?恰好女儿打电话回来,她将这件事对女儿说了。女儿说,你就给他来个以退为进。她说,怎么个以退为进法?女儿说,你直接向他们交一份辞职报告,告诉他们,深圳这边同意为你重新建档,你不要调动手续了。然后,你就装着找人订车票,联系汽车搬家。你如果带着这份报告离开了,交通局不可能再批第二份报告,他们也没有理由找你要回这份报告,那样一来,这件事就黄了。
方子衿知道,这是以个人要挟组织,如果在&ldo;文革&rdo;中,绝对是一大罪行,判刑都有可能。可是,如果不这样,她又能有什么办法?人家摆明了是想玩她。犹豫了三天之后,她拿着辞职报告,走进了局长办公室。局长看了一眼报告,甚至没有全部读完内容,惊得站了起来,问她,你这是么意思?她说,报告上写得很清楚呀,我要辞职。局长说,你不是开玩笑吧,辞职?辞了职,你就么事都没有了。没有工龄,没有退休工资,没有医疗费,没有住房。方子衿说,这个不劳你操心,深圳方面已经说好了,只要我的人去就行,他们为我重新建档,为我分房。而且,他们的工资标准和我们不同,根本不需要套用我现在的工资标准。局长说,有这样的事?你说的不是中国吧?方子衿说,没想到你堂堂局长大人,也这么孤陋寡闻。深圳是经济特区,特事特办,他们的办事方法和程序,和我们内地不同。局长说,这事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需要请示一下上面。方子衿说,请示不请示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我给你辞职报告,只是尊重你。现在,我正式通知你,我只上班到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开始,我就不再上班了。
这方法可真是见效,第二天,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找到方子衿,将一只装香烟的大纸箱递给她。方子衿见到那个箱子,愣了一下,问是什么。主任说,这是你的调动手续、组织介绍信、户口迁移单、粮食关系转移单以及人事档案,全都在里面。随后,他拿出一张表,上面列着每一项手续。他分别将那些东西拿出来,让方子衿验收。最后是人事档案,竟然有十几本之多。每一本上面都贴着白色的封条,盖着人事章。然后,又将这十几只大号的档案袋摞在一起,用绳子捆着,再十字交叉贴了两张封条。其他材料,办公室主任一件件拿出来,摆在方子衿面前,只有这厚厚的一摞档案,他没有动,指给方子衿看看而已。
办完这件事,办公室主任对方子衿说,肖县长让我告诉你,县委组织部的同志和卫生局人事科的同志,明天上午来医院宣布对陆安平的免职命令。肖县长让我问你,还没有么别的要求?
办公室主任离开后,方子衿看着那只大纸箱发呆。那只箱子里有她的人事档案。她还真的没料到,自己的档案竟然有如此之厚。这些档案被两条薄薄的纸条封着,而她必须把这两张封条完整地带到一千多公里之外的深圳。她突然觉得,这两张纸,如同她曾经无数次接触过的妊娠妇女那变得超薄的子宫膜。不,这两张薄纸和子宫膜相比,不知要薄多少。它实在太易碎了。一旦它碎了,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厄运?按照正常的组织调动手续,这些东西,应该通过公文交换或者邮政传递的方式发过去的,可是,他们省了这道手续,破例让她自己带过去,这会不会是一个陷阱?会不会故意让她自带过去中出现破损而造成她一项罪名?显然就是如此,自己要挟了他们一次,他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报复自己。无论是她,或者是杜伟峰,抑或卢瑞国,大概都没有想到,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最后会败在这薄薄的子宫膜上吧。
下班了,她捧着这只纸箱回家,一路上小心翼翼。总算回到了家里,她已经被这只纸箱折腾得筋疲力尽。将纸箱小心地放好,坐下来,她开始发愁。自己要去深圳不难,要让这只纸箱去深圳,也不难。难的却是经历一路上汽车火车的颠簸,怎样才能保护那薄薄的封条不被破坏。
这个晚上她几乎没有合过眼,满脑子都是这个难题。
第二天一早,邮局刚刚开门,方子衿便走了进去,第一时间拿到号牌,拨通了女儿的电话。方梦白没料到母亲这么早会给自己电话,暗吃了一惊,问道,妈,发生了么事?方子衿说,我拿到了人事档案。方梦白说,真的?太好了。方子衿语气中没有半点好的感觉,她说,一点都不好,那些人给我设了一个陷阱。方梦白说,么回事?方子衿将封条的事说了一遍。方梦白说,你别走,等在那里。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他们可能有办法。
方子衿坐在邮局里等了半个多小时,服务员叫道,方子衿,五号。方子衿急急地走进五号电话间,抓起话筒,急急地问,梦白吧?他们怎么说?方梦白说,他们说,你带来好了,只要是单本档案的封条没有坏,就没事。如果你还不放心,他们叫你通过邮局挂号寄出来,如果弄破了,那就是邮局的责任,而不是你的责任。
通过邮局邮寄?如果邮局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弄丢了,怎么办?这东西真的丢了,方子衿可就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无论如何,她不能放心地交给邮局,思来想去,只好将其他所有的东西打包托运,带着这唯一的行李上路了。
辗转到了深圳,女儿和陆秋生在火车站接她。陆秋生是带了车来的,他让司机去接方子衿手里的纸箱。方子衿说什么都不让,一定要抱在自己怀里。陆秋生和她开玩笑,说,是么宝贝?方子衿说,不是宝贝,是我的命。陆秋生以为她是在开玩笑,说,没想到你竟然学会幽默了。方子衿说,我哪里懂得幽默?我说的是真话,这就是我的命。
到了汽车上,司机要把纸箱放在后面的行李舱,方子衿不干,一定要抱在自己怀里。到了女儿的家,进门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纸箱。方子衿往箱子里看了一眼,顿时呆住了,脸色由红转白,迅速白得如纸一般。方梦白看了一眼纸箱,见里面的封条已经碎成了几段,转眼再看母亲,发现她身体在摇晃。她叫了一声妈,连忙上前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