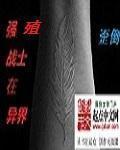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他是一个小结巴番外 > 第65页(第1页)
第65页(第1页)
霍蔓很有眼色地带着车上的人先走了。阮秋小心翼翼地看了霍扬一眼。霍扬自上了车,便紧紧地闭着眼睛,神情里竟然有一种疲惫。阮秋刚想说些什么,霍扬却像是知道他要开口一样,眼睛微微睁开,看向坐在前排的司机说道:“你先出去一下吧。”阮秋心底只觉得一沉。他知道霍扬和自己有话要说,而且是很急迫的话。但阮秋却又猜不到霍扬要和自己说什么话。难道是因为这套高考套卷?应该是的吧……?阮秋心里有些怀疑,但联想起刚才霍蔓在车上的眼神和杨骁说起的“出事了”,稳了稳心神想说什么,霍扬却在他前面开口:“你想告曹鹏吗?”阮秋蓦地抬起头来。他有些不知所措,刚才想好的话也在一瞬间梗回了肚子里。他看着霍扬,茫然地开口:“你知道……曹鹏?”一瞬间脑海中几乎有很多想法迅速掠过。霍扬认识曹鹏?怎么认识的?曹鹏会和霍扬说一些关于自己的、很恶劣的话吗?关于高考套卷的话暂时被噎了回去。阮秋看着霍扬,小心翼翼地开口:“你、你是听到什么传闻了吗?”霍扬没有说话。他打开手机,调出一份文件来给阮秋看。阮秋有些惊讶:“这是……律所?”他之前不是没有动过告曹鹏的念头,可是他没有钱,也请不起律师,打不起官司。而霍扬手机上给出的是一家金牌律所,服务优质的同时价格自然也非常昂贵,是阮秋从来都没想过的存在。“嗯。”霍扬道,目光落在阮秋的侧脸上,“你先看看。”阮秋低下头,那些字他都认识,但此时此刻在霍扬的注视下,他却又什么都看不进去。他又抬起头,呆呆地看着霍扬,犹豫踌躇了再三:“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霍扬的眼睛与阮秋短暂交接,阮秋的目光想要躲开,霍扬的眼却又追了上去。那神情是很平静,甚至是很冷淡的,但眼神却灼热滚烫。他重复道:“你想告曹鹏吗?”阮秋愣住了。他喉头滚动了一下,想说些什么,但最终却什么都没能说出来。他想,他当然想告。那个噩梦一样的晚上,那种令人不适的触感,那些如蛆附骨如影随形的恶意,让阮秋一整晚都饱受着热油烹心般的苦痛。可他有太多牵绊。杨力留给自己的设备他需要好好照看,杨骁还在上学,杨力对自己有大恩,他不能坐视不管。阿婆虽然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可阮秋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这个年迈的老人继续吃苦。他短暂的前二十年就是这样流转于一群和他没有丝毫血缘关系的人们之间:他真正的亲戚舅舅抢走了他母亲留下的房子,抢走了最后一点钱,而和他素昧相识的人们,却愿意燃烧着自己的善意,继续撑起阮秋那岌岌可危即将崩塌下的天。阮秋不是不知道这些。他的苦痛固然让他饱受困扰与折磨,可是他更愿意看到自己拿同样的钱、用从在超市里买来的小米熬好一碗香浓可口的小米粥,给阿婆时,她满是皱纹脸上的开心笑颜。于是他说,算了。“……你都知道了吗?”阮秋看着沉默不语的霍扬,从心里猜测霍扬到底对自己知道了多少。他想了一会,但很快便发现自己想的事情似乎并不重要,于是他鼓起勇气,对着霍扬笑了笑,很轻松地说,“都已经过去了。”阮秋觉得自己很勇敢。他从来没觉得这样轻松过。也许这种事是经常做,伤疤来回撕扯伤口竟然也不会觉得太痛。也可能是因为面对的人是霍扬,疼痛像是完全被麻痹住,他感觉到自己很快乐。他想遮掩的事情霍扬都知道,也许霍扬会误会自己,会像曾经的那些人一样觉得“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亦或是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的话听得太多太多了,阮秋不能说麻木,但是至少在某些时刻,会恍惚觉得那些人说得也许没错。他是一个满是伤口的丑陋的人,但是面对着霍扬,他还是拿起那个厚重笨拙的玩偶服——也许会让伤口变得更糟,但阮秋至少希望霍扬觉得自己比从前好一些。他变得坚强了,他也在努力地向前走。阮秋看着霍扬没有说话,又继续用自己那点少得可怜的勇气说道:“谢谢你,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必要了。”“阮秋。”霍扬望着他的眼睛,“你可以看一看自己的心吗?”阮秋愣住了。“我不需要你回答我其他的问题。”霍扬说,“我是说,阮秋,你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