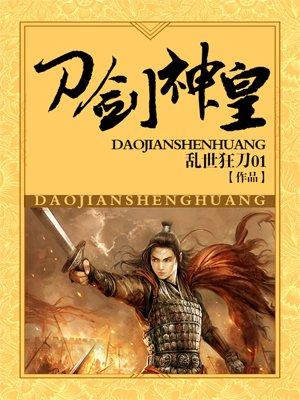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麟台风波录txt云盘 > 第573章(第1页)
第573章(第1页)
“叫你不要提了。”
妇人脸色一沉:“我可是你姐,咱们父母早亡,要不是我把你拉扯大……”
“他心里已经有人了,浅儿嫁过去也是守活寡。”万里云按捺着怒意说。
“只要没过门,他才多大年纪,谁还没有个年少慕艾的时候。浅儿生得,八分像我,但凡是个少年郎,哪有不动心的?”
万里云嘴唇紧紧抿着,听着他姐如同念经一般喋喋不休,脸色越来越难看,猛然一巴掌拍在桌上,茶盏叮叮当当响。
唬得妇人险些跳起来,接着声音却更高了,数落起万里云不尊长姐来。
“万家现在是我当家做主,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你今天不把话说明白,别想出这个门,咱们都别睡了,就这么耗着,明日我是妇人家左右是在家里照料家务,与妇人们闲游赏花。”妇人好整以暇地靠进椅中,摆明跟万里云耗上了。
万里云实在没办法,只有坐下来,朝前倾身,用只有他和他姐姐能听见的声音说:“这个安定侯是个断袖。”
“断……什么?”妇人惊得张大了嘴,勉强自己把嘴闭上,又说,“他只要跟浅儿生下孩子来,安定侯的家业,迟早还不是我们万家的。说起来都是侯,你这个侯,同他那个,可是有天渊之别的。要议亲自然说门当户对,但若是摊开来说,你我都清楚。”
“你就不要想了。”万里云颓然摇头,“他那位可不是什么能养在外面的小白脸。”
“管他是不是,终究是上不得台面的,再说生不出孩子,凭他是谁,百年之后,人虽没了,爵位、家底儿还在。我都给浅儿说了,她不会小心眼,这么好的娘子上哪儿找去。如果安定侯真的是好这口,倒好办了,咱们便把话挑明,只要他们两个和和睦睦做夫妻,生下儿子来继承爵位,旁的都随他。难不成,他们周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东西,到他这里就要全断送了?”妇人嘲讽道。
“他这位,是得皇上保驾的。”
“啊?”妇人笑得花枝乱颤,以手帕沾了沾唇角,“难不成皇上还能为两个男的赐婚?”
“你怎么知道不会?”万里云加重语气问他姐。
“这……这不是枉顾纲常伦理……”
“什么是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总之这事姐姐就别提了,浅儿知书达理,大家闺秀,又姓万,不愁找不到好夫家。”
妇人嗤之以鼻,总算没有再说,心念一动,朝万里云问:“他那位究竟是谁?”
万里云是知道他这个姐姐,不说真能缠一整晚,他也累得慌,唇缝里吐出两个字来:“陆观。”
妇人一愣。
“这……”她不解地皱眉,“皇上也真是心大,这两个人,一文一武,一个有兵,一个有权。天家也不怕……”
万里云沉吟道:“姐姐妇人家,就不要管朝堂上的事。现下我封了侯,司马家怕是要恨上咱们家了,往后你与司马家的也少来往。越是得到封赏,越是不能大肆宣扬,否则这点荣耀,皇上要收回去,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情。”
“知道了。”妇人心不在焉地捏着帕子,端起茶喝了一口。
☆、离合(捌)
眨眼就到了中秋,宋虔之又收到陆观一封家信,说已到容州,联络当地人民的运动进展顺利,军队隐蔽在城外,没有同阿莫丹绒正面遇上。
陆观的家信从来不提龙金山和刘雪松那面的战况,这些宋虔之可以从军报里得知。其间龙金山与坎达英短兵相接一场,楚军略有伤亡,阿莫丹绒派兵在宴河北岸筑起简易瞭望哨,大军退到容州城外与容州留守的军队汇合。
宋虔之一时没想明白,阿莫丹绒在容州留下的八千兵马,城内肯定堆不下,这些骑兵是一人一骑,就算人能留在城中,也没有地方牧放这么多马。
陆观带的人再少,也很难在城内外到处是游兵的情况下隐蔽。于是回信中宋虔之提了一句,问他现在到底带兵多少。
信发出去之后,当日夜里便是中秋宫宴。由于北方战事,李宣下了一道诏书,缩减行宫用度,中秋宫宴也只是赏月、吃月饼,免除舞乐。君臣尽欢后,不到亥时众臣就纷纷出宫,李宣留下宋虔之在行宫。
·
中秋之夜,容州城一改往年赏花灯的习俗,家家紧闭门户。
这天夜里也看不见月亮,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比起去岁遍地灯河,满街的人摩肩接踵,今年可谓秋风扫落叶,满眼萧索。
有的人家做了月饼,也只能一家人围着小桌,苦涩地分食。城外的人进不来,城里的人出不去,团圆佳节也没了滋味。
半夜里容州城上空一声惊雷,所有人都见火光闪过天际,继而城西南方向腾起熊熊烈火,将半边天燃烧成血色地狱。
后院里前几日已经住下的“远房兄弟”们,操起兵器,将水缸、锄头、石磨等能挪动的东西都堆在瓦房门前。
主人在屋内听见外面的陌生人说:“不要出来。”
接着便是匆促的脚步声。
孩子在床上醒来,肉手抓着被子边缘,大的带着小的,母亲轻轻哼着歌谣,回答小孩的恐惧。
汉子们拉开房门,闪出门外,抄起锄头。家家户户在数日间暗地里在卧房另一头都留出了小门,以备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