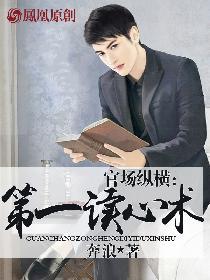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双钗缘免费阅读 > 第61页(第1页)
第61页(第1页)
正垂着头,忽然又有一盏孔明灯徐徐升天。身后传来脚步声,有人笑着说:“我许愿,某人能笑口常开,每天都能看见又圆又胖的月亮。”清懿此时还不知道,这句话在未来很久的某一刻得到印证。那时,他画了一副又大又圆的月亮,送来与她,坦然道:“挂在卧房床头,每天都能看到。”不过,现下的清懿倒不清楚他的无赖还愿法。她只是猛地一回头,然后怔住。不知何时,身后的小丫鬟没了踪影,四周无人。只余那人如芝兰玉树,正负手而立,笑看着她。那一瞬间,她知道,自己的心短暂地失控。片刻后,她复又冷静下来,躬身行礼道:“上回,想必丫鬟已同您说清楚了。我这个人向来如此,喜欢没法装不喜欢,不喜欢也讨好不来。袁公子光风霁月,心中磊落,我却不能同等待您,势必索求更多。你既能体贴女儿家的难处,自然能晓得我的道理。”“对猫儿狗儿施舍的怜悯,倘或施舍给我,不过教我有片刻温暖,却不能聊慰终生。故而,我不如不要,孑然一身,没有挂碍才好。”夜色朦胧,只余孔明灯留下的熹微亮光。那人看了她许久,才缓缓道:“倘或我不磊落呢?”没有得到预料之中的答案,清懿愣住。他看向夜色掩映下,只余浅浅峰形的亭离山。“你从头至尾就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待你好,却不告诉你,是为你有退路。”他的声音伴随山风裹挟的穿林打叶声,略显寂静,“我待你好,是我心之所愿。可我却不能因为我这份一厢情愿的恩情,诱导你错认自己的喜欢。”“你可以因着一个人与你性情相投喜欢他,也可以因他的相貌、他的才华甚至他的风趣喜欢他。却绝不能是因为对你好。”他说这话时,神情竟有几分郑重,“你长在闺阁,善良单纯,有人待你好,你便轻易感动,觉得那是喜欢。可真正的喜欢是灵魂吸引,互为知己,而不是廉价的好。”“我不告诉你,是因为我不要你知恩图报。倘或有一日,你遇着真心喜欢的男子,又愧于我的恩情,届时你该如何自处?”这一番话说完,清懿难得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她从未品尝过所谓感情的滋味,这一刻,她竟无师自通地知道,有人的爱,是温柔妥帖,事事周全的爱。“你说……你不磊落……”清懿故作镇定,抬头问,“这句话,是甚么意思?”他不避不让,同样直视着她,“我心里有你的意思。”这记直球打得她猝不及防。那人一撩袍角,席地而坐,然后仰头看她,拍干净身旁的草地,笑道:“站这么久,累不累?过来坐。”清懿顺从地在他旁边坐下。他望着月亮,揶揄道:“自你同我递话后,我三天没睡好。”清懿没忍住,轻笑出声,“倒不曾想我有这等魅力?竟教游遍芳丛的袁公子也有今天?”“游遍芳丛?”他有些匪夷所思,“我的名声到底被败坏成甚么了?”“约莫是半个女学排队嫁你的程度。”“阿弥陀佛,不能因为一副好皮囊,便污人清白啊。我也是好人家的干净郎君啊。”袁兆故意摆出一副无奈的样子,果然将清懿逗得捂着嘴笑,“那你怎么还敢对我这个花丛浪子托付心事?”清懿笑得满脸通红,想了想,才认真道:“因为,一个身居高位,却能心怀天下的人,到底有几分君子气度在。”闻得此言,袁兆也收起了逗趣的心思,他的眼眸中倒映着月亮,目光寂静。“大武朝既是我的国,亦是我的家。如今它已有病灶入体,沉疴难愈。我师从颜泓礼,虽承了习画的名头,他却授我仁义礼,教我体会众生疾苦。我曾在他病逝前,立誓还武朝一个清明,再去考虑成家之事。”他顿了顿,“而你,是一个意外。”“我虽出身高门,可在周旋于权贵之间时,也需步步小心。”他目光幽深,“他们能接受一个闲云野鹤般的小侯爷,却不能接受有入仕之心的权贵。更何况,我和他们从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清懿没想到他会将这些心底的隐密,对她和盘托出。朗月清风下,恍然间,她好像窥见这人内心的一丝缝隙。她难得鼓起勇气,有些忐忑道:“我虽为女子,倘或你不嫌弃,我也能用心学些有用的,做你的助力?”袁兆笑了笑,朦胧夜色里,他神情柔和地不可思议,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视。良久,他却道:“我不想你踏进这滩浑水。”没有睡好的那三天夜里,他计划了太多的未来。他这个人,一向谋定而后动。他考虑如何突破门阿尧◎妹妹有朋友啦◎“你问我是否觉着程奕愚蠢,答案是也不是。他愚蠢,在于以为一颗真心便可敌一切。殊不知你与他在世人的愚见里,地位不甚匹配。倘或有一日,你真的做了程家妇,他上有心机深重的母亲等着算计你,下有不成器的各房亲戚拖累你。”他忽然定定看着清懿,眼底难得显露一丝真挚,“你是极聪明的女子,即便你百般藏拙,我也知你胸中有丘壑,怎甘愿来程府做一只笼中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