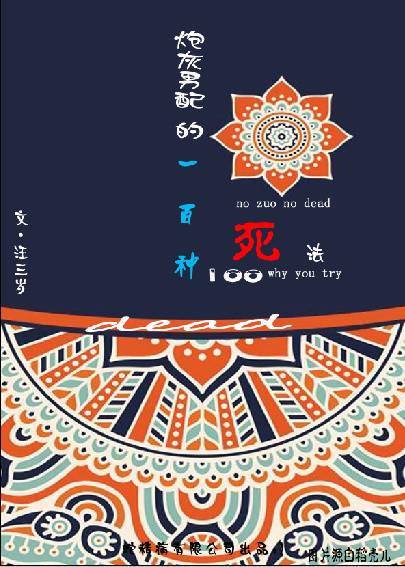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万历电视剧 > 第五节 斗枢恨天(第1页)
第五节 斗枢恨天(第1页)
张懋修听完默然无语,涕泪交加起身长揖道:“无想现今满朝皆罪的涛声之下,在此辽东偏远之地竟有人对家父了解如此之深,惟时代父行礼。”
“斗枢先生不需如此,天道昭昭,历史会证明一切的,会证明太岳公的伟大;我再次请问先生您恨吗!?”龙天羽虚扶起张懋修引入座中又问到。
张懋修低头半晌,骤然抬起头来钢牙紧咬,双眼血红,声嘶力竭用双手捶这椅子的叫到:“我恨!?哈哈哈,我恨这苍天不公道,我父一心为国,却被小人污蔑,生前一心为国,死后尸身还要再次受辱无法安宁于地下;我恨那酷吏为着自己官名不存半点恻隐之心,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我大哥自尽身亡,二哥流放烟瘴之地渺无音讯,老祖母过世无法送终,可怜我哪幼儿才冲龄之年竟被活活饿死;我恨自古最是无情帝王家,用的你时你是宝,嫌弃你时像根草;我恨尽这人间的不公道,更恨我自己无缚鸡之力,不能上不能报父母养育之恩,中不能回馈弟兄间的情谊,下无法延续血脉传承,我就是一无心无肺的废人罢了;恩人您说我恨不恨!?”张懋修说道这里一阵撕心裂肺的大哭,真是见着伤心闻者流泪。
门外王五听闻门内暴喝之声,连忙推门查问到:“公子,你无事么!?”
“没事,五哥麻烦喊人去打盆热水来,拿上条毛巾。”
“是”王五应声而去。
不一会热水毛巾送了进来,龙天羽亲手揉洗了几把双手递给张懋修温声慰道:“斗枢先生千万莫再凄苦,逝者已逝;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人总是要活下去;当务之急是要助先生族中子侄脱困才是,还请先生休书一封,我派了人去江陵接先生族人,摆脱朝廷监视,分批分次转移了出来。先到泉州,再一路海程送来与先生相聚,就在我这里住下,虽不能求的什么富贵,温饱有加还是做得到的,至于先生还请伴随我的身边,让小子早晚得以请教学问。”
张懋修闻言,脸色一阵青一阵白,,默然无语半天,翻身拜伏道:“家破人亡,再惨还能惨到那里去呢!?公子如能救得晚生家中脱离大难,今后但凡公子有所差遣,张氏族人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如违此誓,祖宗英灵永世不得安息。”
龙天羽连忙上前双手搀扶起张懋修连声言道:“万不敢如此,万不敢如此,先生请起,言重了,但求能早晚聆听先生的教诲,我就很满足了,至于先生家难,还请先生放心,我必然尽全力保全。”
转过身来唤到:“人来,速扶张先生归房休憩;一切供应体制依照我的惯例,不可有半点懈怠,要不小心揭了你们的皮。”
说完接着对张懋修说道:“烦请先生休息,某日后还要多多仰仗先生。”
张懋修也不多话又一长揖,随着家仆休息去了。
龙天羽刚刚坐下喝了口茶歇了口气,想着当前的局势心中一阵烦闷,他今年才不过十九岁,同年龄的许多人都还在无忧虑的过着自己的生活,他已经要撑起数万人的产业,又碰此危局;一股如大山般的责任担在肩膀之上,压的有些喘不过气来。
龙天羽决定出去走走,冷静清醒下头脑来计算下一步的行动;他站起身来慢步走出门外,身处回廊边的王五见状走了过来躬身听候差遣,龙天羽对他微微一笑说道:“不出门,就在堡里转转。”
两人顺着回廊走出了院门,刚来到堡前校场附近,就听到一阵吵闹,龙天羽皱了皱眉说:“五哥去看看,还有没有规矩了,怎么如此吵闹,看看是谁如此喧哗,带来见我。”
“是,公子!”王五领命而去。
袋烟工夫,王五领着管家柳江和名两米多高的壮汉走了院中道:“禀公子,是柳江与此人争吵。”
就见这二人跪倒在地口称:“见过少爷!”
龙天羽眉头一皱道:“你二人因何争吵?柳江你也是家中的老人了,怎么如此没的规矩,莫非是忘了家法不成!?”
柳江急惶伏地道:“少爷明察,万不是小的与人争吵惊了公子的驾,实是此人无理取闹,让我无法管束。”
柳江身后跪着的哪名光头大汉嗡声嗡气的道:“这位老爷,今天早上俺在山上砍树,正扛着一颗准备回家,有位白发老头看着我说我力气很大,问我家中有何人,我告诉他我自幼丧父,而母亲上个月死了;他问我愿意不愿意来山脚下的柳家堡当差,我就问他管不管饱,他说管;我又问,给不给老婆,他说给;我就跟着他回来了。好嘛,进了堡把我一丢人就不见了,这大晌午的也不给饭吃,又不给老婆,又不让出堡,我和这小鸡个子才争吵起来。”
“回公子,此人是老祖宗从山上带下来,因没吩咐如何安排,小的们也不敢妄动,按府里的规矩,一天是两趟吃食,现如今才到晌午,小的也不敢擅自做主。”柳江一脸无奈的说到。
龙天羽看着光头一副憨厚的摸样,觉得分外好笑问道:“光头你叫啥!?以前是干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