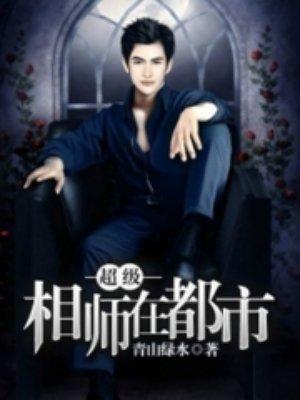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慢慢吟唱 > 第80章(第1页)
第80章(第1页)
一些心肠软的妇人哭了起来。&ldo;哭(尸求)的啥?!&rdo;各自的男人喝止了她们。&ldo;让他捡条狗命算便宜了他。&rdo;
南先生就这样,一直跪到会议结束。他是真诚地向这个收容他的小山村道歉。
人走净了,只剩下翁上元和南先生俩人。翁上元给南先生松了绑,把他搀了起来,&ldo;肏,这叫咋回事哩!&rdo;翁上元感叹到。南先生抹了抹脸上的血,朝他古怪地笑了。
这是后岭开展运动以来,开得最成功的一次批斗会,因为人们唯一一次动了真情。
批斗会平息了人们的怨气,找回了翁家人的面子,也公开了南先生与翁七妹的秘密恋情。南明阳教授可以大摇大摆地步入那座翁家小院;他虽然背上了不好的名份,却得到了坦然的爱情。他知足了,他高兴了,甚至感到了某种意义上的解放。
他装好了一嘟噜羊卵子,准备下山。冯明亮说:&ldo;南先生,七妹都快生了,你就莫给她吃这玩艺了;再滞了胎气,不好生哩!&rdo;
南先生难为情地一笑,&ldo;我还真不懂。那就留着你老冯自己吃吧。&rdo;
&ldo;咱可不吃那个,整天闻着羊骚还不够,还膻那个;要不是高兴跟你喝两杯酒,咱连动都不动。&rdo;老冯说。南先生就把羊卵子提下山了,逞直提到翁上元家里。
&ldo;嫂子,给炒炒,我跟上元兄喝两杯。&rdo;他自觉地随翁七妹叫上了刘淑芳嫂子。
&ldo;你可别那样叫,你一个大知识分子,咱可受不起。&rdo;刘淑芳说。翁上元也说:&ldo;甭弄得那么亲热,让人感到不是滋味。&rdo;
本来南先生自己叫着就有些别扭,那两个人一说,脸就红了。&ldo;行,就随你们。&rdo;
俩人在一起喝酒,谁也不提批斗会的事。翁上元不可能提,他从来不会向别人服软;南先生也不会提,他觉得那一切,都是他应该承受的;虽然受到了那么大的打击,但他不恨翁上元。
南先生说:&ldo;七妹快生了,你给开个介绍信,我们俩个领个结婚证。&rdo;
翁上元一摆手,&ldo;算了吧,你还想把眼给咱现到公社去;让我在十里八村的支部书记面前怎么抬头!&rdo;
&ldo;那也不能这么过啊!我和七妹怎么也得做个正经的夫妻吧?&rdo;南先生坚持说。
&ldo;啥娘的正经夫妻,简直一对混混儿。咋也就那么回事了,大家伙儿也不会说什么,就凑合着混吧。等你那事有了眉目,你要是还有良心,就把她接进城,也不枉她跟你委屈一场。&rdo;
&ldo;不过,眼下就这么凑合,总让人感到名义不顺;出出进进的让人难以开口。&rdo;南先生说。
翁上元笑笑,&ldo;你倒想得周全,还想到名义;这么着吧,我出面给你置办两桌酒,把家里村里一些掌事的给你请来,喝上一顿,也就算给了你们名份。&rdo;
&ldo;也好。&rdo;南先生说。
翁上元就给置备了两桌酒。请的人都来了,祝贺的话也都说了几句;不过,那酒喝得异常冷清。山里人心里对他有反感,不太乐意接受他。
这一切,敏感的书生都感受到了。他尝到了他的爱情的苦涩。
不久,翁七妹生了。却生了一个怪胎:是一个沉甸甸的男孩。额头很宽,眼睛很大,身胚很圆硕,面皮也白净;可就是鼻子没长全,呼吸困难。
好不容易盼着胎儿出世,却竟是这样,翁七妹大恸,痛哭不止。她娘劝她,月子里的身子可经不住这样哭,你要往远处想。南先生哭笑不得,对七妹说:&ldo;不要太想不开,就当咱们又流了一次产。&rdo;听到这话,翁七妹手足一抽,昏了过去。
翁七妹的大奶子奶水很足,轻轻碰一碰那奶身子,奶水就射出很远。但那小家伙就是不吃;小胸脯艰难地起伏了几天之后,死了。
南先生找到翁上元,&ldo;翁支书!跟我走一趟。&rdo;
翁上元看了他一眼,&ldo;干啥?&rdo;&ldo;那孩子死了,帮我给他选一块地方。&rdo;南先生说。
翁上元苦笑一声,&ldo;一个私孩子,还选什么地方,找背人的地方扔了算了。&rdo;
南先生一震,&ldo;依后岭的风俗,婴儿的尸身不是不能乱扔么?&rdo;
翁上元说:&ldo;那是好生好养的,就你这个,生下来就是罪孽;死了也就死了,扔了了事。&rdo;
南先生眼圈红了,&ldo;他好歹也是条生命;一样的生命也应该一样的对待啊。&rdo;
翁上元不耐烦了,&ldo;去,去,你该咋办就咋办,别再烦我,这几天,我的心气儿也不顺。&rdo;
南先生便一手抱孩子,一手执铁锹,沿着他与翁上元埋过死孩子的路线走。到了那个地方,他呆呆地看着翁上元为自己早殁的孩子垒的那个精致的墓。他哭了。他没办法给自己的孩子垒那么精致的墓。他看一眼那墓,看一眼怀里的孩子:这世界,无论在哪儿,都有不公平的事;即便在人情温厚的质朴山村,也不会给这无辜的孩子以公平啊!他哭,哭得耳鸣眼花。他围着那个山峁转,把日头都转落了。最后他在峁顶上挖了一个深深的坑,把他的孩子安葬了。他没有给孩子拱出墓样,而是与地面相平;那湿润的新土一经风吹日晒,就会彻底消失了痕迹。他把孩子埋葬在自己心中了。他向他孩子的亡灵深深地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