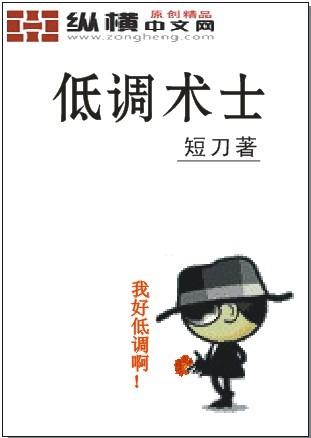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痴情苦一生苦痴情只为无情苦 > 第七十三章吃菜卷轩运忆往事(第1页)
第七十三章吃菜卷轩运忆往事(第1页)
第二天一大早张珊就起来了。
爸爸妈妈刚去上班,她就从妈妈的梳妆台抽屉里拿出口红、眉笔、增白润肤霜之类的化妆品,对着镜子精心打扮了一番,然后又穿上妈妈在省城给她买的那件时尚的连衣裙,然后再在大衣柜的镜子前面一站,镜子里便出现了一位娇艳妩媚勾魂摄魄的倩影:白嫩细腻的瓜子脸,清丽娟秀的柳叶眉,秋波荡漾的含情目,性感迷人的樱桃嘴。再加上脸颊上那一对俏媚甜美的小酒窝,嘴唇下那一粒锦上添花的美人痣,更使其陡增了几分妖娆与亮丽;一袭海军风紧身连衣裙,使其臀部略微凸起,胸脯明显翘挺,玉颈愈显秀颀……虽然她的眼神中还残存着难以消褪难以掩饰的忧郁、愁闷和颓废,但这丝毫不能减损她的妩媚和妖艳,反而使她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
她微微笑了一下,这微笑中没有开心,没有甜蜜,没有幸福,没有愉悦。有的只是顾影自怜的凄苦和万般无奈的幽怨。因为她很清楚,今天如此打扮自己,并非是因为对人生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向往。只是,仅仅只是为了了却一段令人心碎的痴恋,了却此生唯一的心愿。
时令即将进入大暑。烈日炎炎,骄阳似火。大地全面进入烧烤模式。落满了尘土的树叶打着卷儿,没精打采地在热浪中微微颤抖。无聊的麻雀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多情的燕子衔着小虫飞进巢里。满腹心思的轩运焦躁而又耐心地等待着张珊的来临。快乐的时光如白驹过隙,等人的时间似蜗牛爬坡。为了安抚难耐的等待给自己带来的焦急和烦躁情绪,轩运给自己找了一个能让时光加速的差事——保养他那“秦琼马爷爷”。他穿着一件米色圆领汗衫,趿拉着自制的木板拖鞋,圪蹴在院里的大桐树下,面前放着他那破旧的自行车,自行车旁边放着一盆脏兮兮的污水、一块油腻腻的抹布、半玻璃瓶废机油——润滑自行车链条之用。
轩运正擦洗着自行车,不料马立春突然匆匆忙忙地来了。他手里端着一个粗瓷大碗,碗里放着几节菜卷,菜卷散发着香喷喷的肉味。
马立春把盛着菜卷的粗瓷大碗放到轩运旁边的一个凳子上说:“快吃吧,我妈刚蒸的,还热乎着呢——噢,我走啦,还要到我爷爷家里去。”
轩运也确实有点饿了。他顾不得洗一洗沾满油泥的脏兮兮的手,就走进窑洞里,从本子上撕下几张白纸,又匆匆走到放着菜卷的凳子前,用白纸垫衬着脏手,捏起一节菜卷就塞到了嘴里。
真香啊!轩运咬了一大口嚼着,嘴角好像有猪油要流出来。
自从妈妈去世以后,这是他第二次吃到这样香喷喷的菜卷了。妈妈活着的时候,虽然是个病秧子,但她却是个“巧妇”,特别是在饭菜方面,她总能变着花样,把极普通的面食蔬菜做得美味可口。轩运自小爱吃菜卷儿。她就经常做给轩运吃。菠菜便宜了,她就做菠菜粉条豆腐菜卷,胡萝卜便宜了,她就做胡萝卜粉条鸡蛋菜卷。因为经济条件的制约,她很少在菜卷里放肉。妈妈去世后,轩运第一次吃到香味浓郁的菠菜大肉菜卷是在秋燕的家里。那是“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小麦拔节,祭扫踏青的仲春季节。那一天是寒食节的第二天,也是一个星期天,正是上坟祭扫的好日子。轩运与他五服之内的族人们成群结队、翻沟越岭,按照严格的约定俗成的程序,上完了所有该上的坟以后,他就准备到官帽岭上折几枝柏枝带回家——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上坟后折几枝柏枝,回家后系上大红布条,插在大门上。据说这样可以让祖宗的在天之灵保佑其子孙后代如松柏一样四季长青家道兴盛。
轩运走到官帽岭前,看着桃花已经谢落的桃林,突然就想起了曾经与秋燕在此缠绵的情景——一想起秋燕他就难以控制激动的心情,他就心急火燎地想见她。于是,他急匆匆地回到家里,收拾了一下去学校该带的东西,就骑着自行车直奔秋燕家了。
秋燕也是刚刚上坟回来,正坐在桌子前吃菜卷儿。当秋燕的母亲看到自己未来的女婿来到时,显得非常高兴。她先是端了三节菜卷儿放在轩运面前,然后又一边沏着茶,一边对秋燕说:“燕儿,你爸的抽屉里还有一盒好烟,快拿出来!”
秋燕娇嗔地瞅了她妈一眼说:“妈!你怎么这样惯他!学生还能抽烟?”说完,她又对着轩运娇媚地笑了一下。
轩运蘸着放了蒜末的老陈醋,吃着菠菜大肉菜卷子。秋燕的妈妈就一直坐在炕沿上和轩运扯着“闲话”。她本应回避的,给女儿和准女婿一点私密的空间,但她没有回避。她并非不懂这些。她是过来人,也是聪明人,能不懂热恋的情人的心思吗?只是大女儿秋丽的惨痛教训,使她产生了“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使她至今还心有余悸。她担忧这个又帅气又聪明的小子考上大学后又像大女儿秋丽恋爱的那个坏了良心的千刀万剐的“陈世美”一样,把秋燕给踹了,使秋燕重蹈大女儿的覆辙。她本来是不同意这门婚事的,可她拗不过自己的宝贝女儿。她怕秋燕那种对人难以启齿的丢人洒醋的病又发作起来,加之有朱老师做媒——在她的心目中,先生是神圣的,先生的目光能看清一切能看透一切,先生是不会看错人的。正因如此,她和老伴经过一番分析研究后,也就勉强同意了。轩运到她家来过几次后,她感到这个尚未过门的女婿不仅手脚勤快,而且很本分很懂事。说话做事都很有分寸,并非那种说话三丈高二丈低,做事毛手毛脚的花里胡哨的浪荡公子。于是她心里就欢喜了许多,也踏实了许多。但她还是有她的老主意——不管怎样,该提防的还得提防,该敲的警钟还得敲——她旁敲侧击地说,正月的时候,她到邻村看了几场戏,那是地区的蒲剧团演的,唱的可好啦!特别是有一出叫什么《铡美案》的戏,真真是教育人,那个叫陈世美的坏家伙,坏了良心,连老婆孩子都不认了,不要了,结果被青天大老爷给铡了。还说她娘家村里有个小伙子原本也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后来接了他爸爸的班,进工厂当了工人,吃起了公家饭,有了几个臭钱,就这山望见那山高,看不起家里的原配媳妇,和厂里的一个女娃娃好上了,和家里的媳妇离婚了,可谁知那女娃有羊癫疯,一直瞒着那小伙子。结婚还没半月就犯了一次,犯的时候,她正骑着车子,结果就摔倒了崖下,摔坏了一条腿不说,枣刺还把眼窝扎得流了水,一只眼窝也瞎了,把那小伙子后悔的呀,肠子都悔青了,可他也是自作自受……
“妈,你说那些干啥呢!”秋燕红着脸看着她妈埋怨道。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不过年轻人到了外边花花绿绿的世界,可千万不能看花了眼,鬼迷了心窍,做出没良心的事,那是要遭报应的……”
秋燕妈好像有点刹不住车了。
“妈!妈!你怎么又说开了?不要说了嘛!”秋燕噘着嘴,眼里含着泪花,扭过了身子。
轩运开始吃那热乎乎香喷喷软囔囔的菠菜大肉菜卷子时,感到好吃极了,蘸着漂浮着蒜末的老陈醋,不知不觉就把两节咥进了肚里。可随着秋燕妈妈的警钟越敲越响亮,越敲越刺耳,他就无心再品尝那美味可口的菜卷了,他在细细地品味着准丈母娘的每一句话。他在第三节菜卷儿上咬了一小口就停住了。他左手拿着菜卷儿,右手放在桌子上,凝视着面前飘着蒜末的老陈醋发呆。
秋燕带着哭腔的责备妈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他扭过头就看见了秋燕绯红的脸颊、晶莹的泪花和高高撅起的红润的小嘴。
轩运把目光从秋燕脸上收回来,然后它又穿过屋门,穿过院子中央,最后就落在了院子墙角的一棵杏树上。杏树很大,苍老的树干和枝桠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但上边依然结着许多绿茸茸的状如青豆的小杏。
轩运尴尬地笑了一下,目光依然停在屋外的杏树上。他说:“妈,你的意思我知道了。你尽管放心,我绝不会做糊涂事,更不会做坏良心的事,你要相信秋燕的眼睛,她是不会看错人的!”
轩运吃着马立春送来的菜卷子,回忆着他在秋燕家吃菜卷儿的情景。突然,“哐啷”一声大门开启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他迅疾抬起头,一位时髦靓丽的美少女便进入了他的视线,紧接着一缕娇柔甜脆的声音又飘到了他的耳畔。
“轩运,轩运!”
张珊?张珊!哦,是她,就是她!——尽管来者的装扮使轩运感到惊诧,但他还是在一瞬间就完成了疑惑——辨认——确定的程序。
“张珊!珊,你总算来了!”轩运疾步跑过去接过了张珊的自行车。
“你家里人呢?”张珊看着轩运轻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