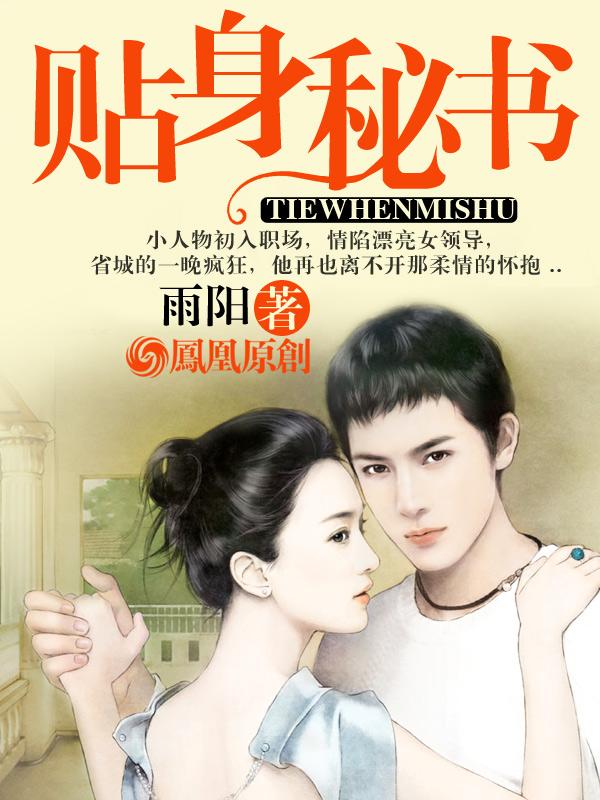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阴阳当铺免费阅读 > 番外 浴血一(第1页)
番外 浴血一(第1页)
(昨天是小竹子的生日,特以此番外送予她,撒花~(≧▽≦)~啦啦啦 这是第一卷的番外,背景可以追溯到刘丰年和风浅夏的相知相遇……
不知道这两人是谁的筒子们,请自动面壁(  ̄  ̄)σ…( _ _)ノ|壁
另:本文以第一人称为主,我即‘刘丰年’)
这是三个人的故事,我,他还有她。
三个人的故事,可以很小,小到只有那小小的院落,小到只有三个人的嬉戏打闹,小到可以无视成人的烦忧,撇去纷争的血腥;三个人的故事,也可以很大,大到拥有整个中原大陆,大到可以囊括大半史书的传奇战役,大到能够尝尽人生百苦,看破万丈红尘。
如果可以,我想祈求上苍将时间永远定格在那小小的院落,而不是现在,我功成名就,坐在那冰冰凉的高位上,俯视台下几十甚至数百张千篇一律的面孔——谦卑,虚伪,敬畏……重复度如此之高,高到让人想吐。
突然开始有些怀念,怀念那个站立如松的男子。
他总是静静地立在自己身侧,面容收敛,甚至是有些肃穆的,若是自己出了一个荒谬的主意,他定会面无表情地指出来,完全视君王之威于无物。那君子坦荡荡的作态,总是让人觉得自己还是那青葱少年,鲁莽不可知物。
他总是对的,只是——他的话越来越少了,在朝堂之上见到他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见了?
对了,还有一个人,那个,她。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年少时那喜欢将头发高高竖起的野孩子,她总是脏兮兮的,爬树,掏鸟窝,比我们男孩子都野。
我时常怀疑为什么静默如盘松的他会和好动如脱兔的她走在了一起,直到那一日我懂了。他得知她被流窜的胡军掳去,手腾地一紧,他最爱的青瓷茶盏便在他手里碎了个彻底。
而他顾不得尚在流血的手,就冲了出去。那时外头尚在电闪雷鸣,倾盆大雨灌得他满身都是水,他却疯了似的疾奔到马厩,手中的马鞭甩得劈啪作响。
他那匹玉骢马被他折腾得只剩下半口气,就是不肯挪步。马都是有灵性的,它不动自有它不动的理由。
我拦住了他,却是被他充血的眼吓了一跳。他从未如此失控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怀疑他根本没有生而为人的感情,只因他从来都是淡漠的。
我没见过他发脾气,甚至是姽婳那疯丫头将掏下来的鸟蛋失手甩了他一脸,他都只是漠然地将其拂了下去,连眉头都没有皱过。
她唤风浅夏木鱼脑袋,风浅夏那厮也只是抬了抬眼皮,惹急了才把那疯丫头拎起来,有时候是甩在水池里,有时候就干脆把她一掌劈晕了省事。
打打闹闹,就像是他们之间的交流方式。一个叽叽喳喳,消停了一会儿就难受,一个缄口不言,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一个疯疯癫癫,上蹿下跳,一个无甚脾气,淡漠安静……
现在想想,倒也绝配。
只是那时候的情况,容不得这其中的儿女私情。
我清楚,他了解,但我比他看得更清,只因为他才是那个局中人。姽婳,那个火一样的美丽女子,注定是要被牺牲的……
我想的到的他自然也能想的到,可想的到是一回事,能不能冷静下来淡然接受是另一回事。
而我,只能做那个注定讨人嫌的。因为我,只有我,才能在这个时候打醒他,即便打醒他的代价,便是失去了这多年的情分。
胡军乱贼掳走姽婳定是要以此作为要挟,而如今的我们根本分身乏力。
最后一战了……
大局在前,岂能有失?!更何况敌军手里的底牌只是一个人,一个女人,虽然对于风浅夏而言,姽婳于他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个女人该有的范畴。
而超出范畴的存在,注定就是他的软肋。
但是,人力,物力,军民的精神状态,粮草的储备……各种因素都在告诉我们——没有时间了。如果此时风浅夏离队,定会带走大批的人马;即便不然,风浅夏只身一人前去也是凶多吉少,逮着了风浅夏,他们也算不得亏本。怎么算,我们这边都是要付出承重代价的,而对于已经付出过无数血汗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再也负荷不了的。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覆水难收,而我们已然无法回头。走到如今这一步,我们都已然耗尽了心力。说我自私也好,野心也罢,这脏活……
我定是要抗下的。
“大军逼近,你这是做什么?!”我听到自己如是朝着他吼道,“你想死我不拦你!你可曾为誓死跟随你我的那些人想过半分!!”
平时冷得跟冰块似得人一旦激动起来,神佛都挡不住。更何况被这大雨一浇,他似乎又狂躁了几分。
我学过些拳脚功夫却抵不上他多年的精练,只不过他现在处于失控状态,挣扎起来丝毫没有章法可循。但仅仅是这种无意识的挣动,我都觉得我自己的手臂快被他扯裂了,疼痛自手臂传导入脑内,冷热交替之间,大脑却是清醒得很,清醒得钻心地疼,神经性质的疼痛反馈到我那冷得有些发抖的唇,就成了破口大骂——
“你***给老子清醒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