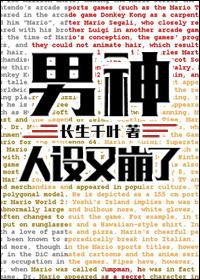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男主是个黑切白 > 第85章(第1页)
第85章(第1页)
为什么要做这种惹人嫌的事。况且,他在屋外也能听清里面的动静,而外头也确实需要他镇镇场子。
白芨引凌月婵一同进了屋子。
“阿芨!”一进屋,凌月婵就拉住了白芨的胳膊,恳切道,“你确是被那歹人威胁了吗?你不要怕,照实告诉我。我天蚕派弟子数万,没有眼睁睁见歹人作恶的道理。我们……我一定能保护好你。”
白芨看着凌月婵,心中泛起暖意,又骤然冰冷了下来。
她这样真心待她,都是因为她不知道她做了什么。
复杂的感情交杂,愧疚和难过压得白芨有些喘不过气来。
白芨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拉着凌月婵坐下,道:“月婵,我有话要对你讲。”
“嗯,我听着。”凌月婵把椅子挪到她的身边,与她肩并着肩坐着,道,“你不要怕,什么都可以和我说。”
白芨斟酌了一下措辞,决定和盘托出。
就算伤人也好……毕竟是凌月婵家的事,凌月婵有权利知道一切,也必须知道一切。接下来,需要控制住局面的,也得是她。
于是,白芨开口,道:“月婵,你可知你家家业,是如何来的?”
“自然是,我父亲经营有道。”凌月婵道,“他与武学上并不出挑,经商的本事与气运却是一顶一得好。”
“那你可知,他的气运是从何而来的?”
“这……气运,哪有从何而来的道理?”
“他的气运,来自于蛊。”白芨道,“金蚕蛊。此蛊能使家门兴旺,于生意场上所向披靡,万事亨通。却也食人……每年需食一人。你家挑选去绝情谷的人,实际都已经被喂给了蛊虫。就连所谓‘绝情谷’,都只是个掩人耳目的地方罢了。”
听着她的话,凌月婵皱了皱眉头,道:“这话是谁说于你听的?可是那歹人?真是天方夜谭,简直将我天蚕派污蔑得仿若魔窟一般。阿芨,你不要听人胡讲。我父亲性格是刻薄一些,但绝不是这种恶人。这里头,必是有人在刻意污蔑!”
白芨没有反驳。她看着凌月婵,眼神温和又哀伤。她开口,继续道:“我今日所刺死的,就是金蚕蛊。依赖蛊虫的兴盛,从不是真正的兴盛。因而,蛊虫一死,不出一年,你家盛况就会消失殆尽,半点也不复存在。也许会恢复成养蛊之前的样子,也许会连那也不如。”
“……你在说什么。”凌月婵看着白芨,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离谱的话。
白芨看着她。
“月婵,你可以恨我。”白芨道,“你应该恨我。”
这是她第二次说出了这句话。
凌月婵忽然感觉脑子很乱。
她一点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可是,白芨的眼神有那么认真。
说到底,是她不相信,还是不敢相信?
验证真伪的方式很简单。只要看看天蚕派是否会真的随着一条虫子的死去而飞快衰落,只要看看所谓的“绝情谷”是否真的存在,看看被送去绝情谷的弟子是否是真的在随高人习武。
凌月婵的脑子很乱。
凌月婵忽然感到了莫名的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