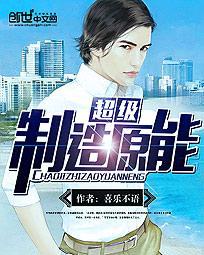怪力小说网>穿越后我成了将军府夫子免费阅读 > 第13章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3章(第1页)
此时千里之外的江州。
连日的暴雨已经将整座城淹成了一片汪洋,泥黄的江水中,随处可见一片狼藉。倒塌的房梁、折断的树枝,飘浮的衣物、被冲上岸边死去的家禽鱼类……就连寺庙也没能幸免,金箔塑身的铜像半泡在水里,许多地方都已皲裂脱了壳。
幸运的百姓在洪水淹城前逃了出来,投奔到别处的亲人家里;别处没有亲人的,则徒步几十里,来到临近的荆城避难;那些未来得及出逃的不幸的人,生命便就此终结在了这茫茫江水中。
荆城府衙内。
府尹赵德成像只热锅上的蚂蚁,在偌大的前厅内来回打着转儿,从客位走到主位,又从主位走到门边,脚下的地砖都快磨出了一道道印子。他边走边右手握拳捶一下左手掌,隔了一会儿又左手握拳捶一下右手掌,面上愁苦得快要淌出水来,心里的咒骂一直没停下来过——
该死的冯天志!晓得事情不妙便早早收拾金银细软拖着全家跑路,留下一堆烂摊子让他收拾。现在城外全是江州来的灾民,闹着要进城,他这城里哪儿能装下这么多人。朝廷的赈灾银粮又还没到,外边上千张口等着吃饭,叫他打哪儿去弄来这么多救济粮。再这样下去,那群刁民怕是明日就要砸门了!
该死的小人!懦夫!王八蛋!
虽然预料事后冯天志这江州太守的乌纱帽是铁定保不住了,不仅保不住,小命或许都得丢掉,但他还是想再往上参他几本,在他的罪名上再多加几条,落个死不留全尸最好!让他没给他好日子过!
赵德成恨恨骂着,鼻子哼出的气快把两撇稀疏的胡子吹上了天。
忽然门房急匆匆跑来,跑得太急还差点被门槛绊倒,边跑嘴里边高声喊道:
“大人!大人!”
赵德成思绪被打断,暴躁地转过身,“嚷什么嚷!没看我正烦着吗!”
“大人!外边来人了!”
“来什么人,都是些刁民,赶出去!不见!什么人都来烦我。”
“不、不是啊,好多人,好长一段车马队伍,好像是、好像是朝廷派来的人!”
“朝廷派来的?”他眉毛和眼睛登时挑高。
“领头的可有说是谁?”
“不清楚,好像是……什么王爷。”
王爷?
他惊了一下,这朝廷派来的钦差怎么会是个王爷?哪一个王爷?
他揪着胡子思索了两下,随即催促道,“快,领我去见。”
“哎!”
前厅离大门不远,走不过几十来步便到了。两扇朱红色大门打开,外面的确是浩浩荡荡的一条队伍。
领头的站了两个人,个子矮些稍靠后的那个着一件青色水纹绨,头戴一顶黑色平头小帽,面白无须,一看便知是个内侍;领头的那位弱冠年纪,一身深紫锦袍,腰间别一蒲纹玉佩,袍上绣着的四爪龙十分抢眼,脚踩金线靴,头顶翡翠冠,虽然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风尘仆仆,周身华贵不凡的气质却无法掩盖。
这个年纪的亲王,身边常随一眉清目秀的内侍,又被派来接手这种苦差活儿,那只能是……
“下官赵德成,参见霖王殿下——”
赵德成心思转得飞快,眼珠子一转,只一瞬,便高举起双手,双膝下跪匍匐在地,嘴里高喊着参拜。
司马琰瞥他一眼,“起来吧。”
“谢霖王殿下!”他站起身,“王爷远道而来,下官有失远迎,还望王爷恕罪。下官即刻便差人收拾屋子,备上热水。王爷舟车劳顿,想必腹中已是饥饿,待您梳洗一番,下官斗胆设宴摆席,府内虽简陋,却断不会让王爷受腹脏之苦。如若王爷不喜,也可移步城内最好的酒楼,那里……”
“不必了。”
司马琰出言打断他的喋喋不休。
赵德成看见霖王眉心轻皱,他身旁的小太监也露出了一副鄙夷的表情,这才讪讪住了口。
“本王方才来的途中,看到城外路上皆是尚未得到安置的江州民众,许多人多日未进食,性命已垂垂,里面还有不少孩童。赵府尹有那时辰宴请本王,不如先把眼前这事解决了吧。”